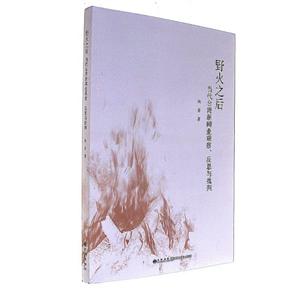-
>
妙相梵容
-
>
基立爾蒙文:蒙文
-
>
我的石頭記
-
>
心靈元氣社
-
>
女性生存戰爭
-
>
縣中的孩子 中國縣域教育生態
-
>
(精)人類的明天(八品)
野火之后-當代臺灣新聞業觀察.反思與批判 版權信息
- ISBN:9787510858192
- 條形碼:9787510858192 ; 978-7-5108-5819-2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野火之后-當代臺灣新聞業觀察.反思與批判 內容簡介
本書以臺灣民主轉型中的新聞傳播制度變遷為研究對象,通過對臺灣新聞界、學界人士的訪談,展現臺灣民主轉型中臺灣新聞傳播的歷史過往和現實,并探討臺灣媒體解禁后的實際狀況,分析了臺灣媒體政治光譜分化、商業勢力極端壟斷、新聞品質下降和媒體視野狹小等現實問題。
野火之后-當代臺灣新聞業觀察.反思與批判 目錄
目錄
序一公共服務媒體必須是領頭羊
序二我們找到星星了嗎?
**章通天塔與不歸路:從報禁到解禁
一、行政管制與自由市場
(一)黨政軍控制媒體和高校內化教育
(二)由硬轉軟的控制
(三)自由市場的媒體亂象
二、侍從媒體與政治合謀
(一)強人陰影下的侍從媒體
(二)臺灣媒體是民主的推手還是權力的跟從?
(三)新政商關系——合謀的伙伴
三、西化影響與本土意識
(一)自由主義思潮對解除報禁的影響
(二)新聞傳播政策制定中的唯西方論
四、新聞傳播政策與良性媒體環境
(一)以“非無限”的自由與合理的管制去除市場之虞
(二)長遠規劃符合本土的新聞傳播政策
第二章野火之后:臺灣媒體市場、行政管控與新聞自由
一、何謂新聞自由?
(一)欠缺共識的新聞自由
(二)作為制度性權利的新聞自由與言論自由的區別和重疊
(三)媒體的自由與民眾的自由
(四)消極的新聞自由和積極的新聞自由
二、臺灣媒體解嚴后仍被詬病缺乏新聞自由的癥結
(一)第四權的適用與局限:媒體的特權與限權
(二)自由放任論的終點:媒體所有權與多元化市場
(三)社會責任論的烏托邦?——人民利益、政府作為與
媒體操守
三、尋路臺灣:新聞自由如何構建?
(一)結構性管制:以權力的制衡來保障新聞自由
(二)合理的社會結構促進媒體多元化和自由度
(三)偏重公共媒體的多元資源
第三章臺灣新聞學界訪談錄
一、鄭貞銘訪談錄
二、馮建三訪談錄
三、林元輝訪談錄
四、林麗云訪談錄
五、蘇蘅訪談錄
六、陳百齡訪談錄
七、倪炎元訪談錄
第四章臺灣新聞業界訪談錄
一、陳國祥訪談錄
二、尤英夫訪談錄
三、何榮幸訪談錄
四、邱家宜訪談錄
五、程宗明訪談錄
第五章臺灣新聞管理界訪談錄
一、邵玉銘訪談錄
二、蘇正平訪談錄
后記
野火之后-當代臺灣新聞業觀察.反思與批判 節選
一、鄭貞銘訪談錄 鄭貞銘簡介 文化大學新聞學系教授(退休)。1936年出生,曾任文化大學新聞系主任,新聞研究所所長,《香港時報》董事長,英文《中國郵報》副社長兼總編輯,臺灣大眾傳播教育協會副理事長兼秘書長。代表作有《新聞原理》《新聞學與大眾傳播學》《新聞采訪的理論與實際》《世界百年報人》等。曾榮獲“中興文藝獎”、“五四文藝獎”(臺北)、“新聞教育終生成就獎”(紐約)、“美國新聞教育特殊貢獻獎”(紐約)、“文化交流貢獻獎”(香港)。 訪談時間:2013年10月22日 訪談地點:咖啡廳 自由與控制永遠是在拉鋸當中 蘇惠群(以下簡稱蘇):提到報禁給您印象*深刻的是什么事情? 鄭貞銘(以下簡稱鄭):我想在進入這個主題之前,我有兩個基本的觀念跟認知說一下:**點是從兩三百年英美新聞史的發展與新聞自由的發展,以及我們臺灣六七十年來的發展,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自由與控制永遠是在拉鋸當中,從兩三百年的歷史去看是處于拉鋸之中,不只是臺灣,從整個人類新聞史來看,過去英美報人多少人為了新聞自由,向政府爭取自由,而犧牲生命,后來英美新聞自由的思想觀念普遍走入民間。我想這個前提的意思不是說自由就是好的,控制就是不好的。其實自由也好,控制也好,都是中性的名詞。我們一方面當然要追求自由,可是你能夠永遠不受控制嗎?父母對你的教育是一種控制,對你行為的管制也是一種控制。我今天坐在這兒,我有伸個懶腰的自由,可是伸出去的手不能碰到別人。所以,西方說自由是以自由觀的鼻子為界,你不能碰到他的鼻子,去侵犯別人的自由。其實自由也好控制也好,都是要去追求“為什么要傳播”這樣一個理想,我們人類為什么要傳播?傳播*重要的就是要溝通、要增進了解。如果說你自由過度,侵犯別人隱私權,你是不是就侵犯到別人了呢?這是我首先要提的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第二個對這個議題很重要的觀念是,所有的自由包括新聞自由都不是天上掉下來的,也不是有權力的人賞賜給你的,永遠都要爭取。所以當自由和控制在對抗的時候,自由退一步、控制就進一步,控制退一步、自由就進一步。所以,我第二個觀念,自由是要爭取來的,不是政府賞賜給你,或者有權力的人賞給你的。對新聞自由的爭取永無隕時,你不要認為我現在已經夠了,因為你說夠的時候就是退的時候,控制的力量又過來了。 蘇:這種對抗是永遠會持續下去的? 鄭:對,要用歷史的觀點去看。也不只是看臺灣的歷史,要看整個人類新聞傳播的歷史,新聞自由的歷史。以上是我的兩個很重要的基本觀點。 臺灣報禁的問題,老實講也是當局控制和新聞界爭取自由的對抗或者是斗爭的結果,為什么有報禁?就是當局要控制新聞界,當局控制新聞界確實也是有當時的背景、理由以及需要的。但是,新聞界爭取自由,臺灣能夠變成今天這樣也是多少人付出的努力,不過我自己個人認為,時空背景的轉變也是一個因素。首先要了解當時臺灣的社會背景,臺灣被日本統治了50年,日本對臺灣也是實行控制,思想控制包括學日文、辦日文報等等。本省的老一輩的人還有人會很懷念日本,這一方面也是受了日本思想、精神控制的結果。 結合臺灣當時的背景,我們要思考一個問題,臺灣今天新聞自由的環境真是得來不易,可是臺灣為什么會變成自由民主思想為主流的一個地方?當時臺灣當局要實行報禁,還有當時時局的關系,比如與中共之間的對抗,我們那時也覺得中共對臺灣的滲透無孔不入,對不對?新聞界的滲透也是其中*重要的滲透之一,后來因為“匪諜”之類的,新聞界也被抓了很多人。在這種情況之下,從蔣公時期有報禁,這有其時空環境和背景,一方面為了保持臺灣的安全,跟中共對抗;另一方面,日本奴化思想還沒有去掉,需要把它去掉。 蘇:我們一般會想到**個,第二個想得比較少。 我們今天用的主要理論還是英美的 鄭:臺灣從那樣一個社會走到今天這樣的自由民主真的是得來不易。第三個是難免的也是事實,就是蔣公個人的威權思想,從他的個人性格還有過去他在大陸的統治等等,我們也可以看出他的威權性格。他當然比較沒有西方的自由民主思想,他是日本受的教育。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講臺灣報禁、報業發展的時候,必須講到臺灣早期負責新聞宣傳政策的幾個重要的人,都了不起,這些人剛好都是我們這一輩的人,他們一方面當然要遵從蔣公的管制路線,但是另一方面這幾個人都是受西方民主自由思想的教育,像馬星野是密蘇里新聞學院的,謝然之是明尼蘇達大學和密蘇里新聞學院,他們都做過第四組主任,也都是宣傳部長,都是直接負責宣傳政策的,還有曾虛白、董顯光。這些人個人受教育的背景和他所了解的新聞傳播觀念的東西,今天老實講,中生代的這一批新聞學研究者從來沒有去考慮這幾位先生對臺灣新聞事業走向的貢獻,一方面他們要尊重蔣公的意志,一方面他們要在各種場合展現應該走向何處。 我在謝然之老師90歲的時候在美國去看過他很多次,有一次他親自跟我講過:一方面蔣公的意思他不能違背,另一方面他要去發展新聞教育的原因是什么?新聞教育我們今天用的主要理論還是根據英美的,他說他做第四組主任、宣傳部長,他也在日本留學過,他比較研究了日本跟美國對新聞事業的兩種思想和態度,他覺得確實英美的思想是比較優秀的,所以就大量引進西方的新聞思想和理論。曾虛白、董顯光這些人其實貢獻很大。馬星野主辦的黨報《中央日報》在發展的過程中有一個時期很有名,叫作“政策的辯論”,就是到底應該“先中央后日報,還是應該先日報后中央”,這是《中央日報》黨報兩大政策辯論。一開始主張國民黨辦的《中央日報》當然要宣傳國民黨的政策、國民黨的思想、總裁言論,當時提出這個主張的代表人物是陶希圣。陶希圣是《中央日報》董事,馬星野是社長,他們兩個就是兩派,馬星野主張“先日報后中央”,你要辦報,你要使你這個報紙被讀者接受,讀者喜歡看你的報,相信你的報,在報紙的公信力建立之后,所登的東西讀者才會相信。 蘇:陶希圣與馬星野的觀點剛好相反? 鄭:陶希圣是黨中央思想的重要管制者,為什么馬星野會提出這個呢?那時候想要求變不是很容易的事,他是忠于自己的理想、自己所學和自己的信念。謝然之為什么說日本那套不行,還是美國這套好?他在日本和美國都有留學經歷,他對日本奴役臺灣50年后遺留下來的問題是高瞻遠矚的。 蘇:在我的印象中陶希圣不是學新聞的。 鄭:對,他沒有學新聞的背景,也不是留學美國的,所以他是傳統的黨的思想管制者。現在中年學者,都不太了解這一段歷史和這些人物,我早期比較幸運的是在馬星野身邊做了三年多的事情,他在中國大陸辦《中央日報》,任中央政治學校新聞系主任,在臺灣沒有教過一天書,但是我為什么對馬星野思想那么了解?我們辦了一個“中華民國大眾傳播教育協會”,他眾望所歸擔任理事長,他提名我做秘書長,后來過了三年,他又提名我和徐佳士做副理事長,我跟了他三年,真正比較了解。謝然之老師,在政大時是我們**任系主任,后來到文化大學又創辦新聞系,我到美國曾多次和他深入的切磋思想。 追求一種對未來的向往 蘇:您當時以**名考上新聞研究所,大學部是第二名考上,請問當時臺灣政治大學新聞教學理念是怎樣的?像王洪鈞、曾虛白,這些前輩是怎樣講述報禁的?提到的時候他們的觀點是怎樣的? 鄭:基本上像謝然之老師,還有講“中國新聞史”的曾虛白老師,他們當時都是黨的重要的文宣政策的制定者,尤其是他們在宣傳部的角色,在政治上會為黨實行的報禁說很多的理由,講當時不得已的原因,比如“國家”安全。其實,真正影響我思想的反而是他們在談新聞學概念、西方概念的時候,不露痕跡地讓你知道自由民主是會還是不會?新聞自由是會還是不會?意思就是說他也為黨的政治來辯護,但是他更讓你去追求一種對未來的向往。因為他們預計當時實行報禁的這幾個政策,可能慢慢隨著時光都會轉變,為實行報禁而具備的理由都不是永恒的真理,只是因為當時客觀的情況而不得已。 蘇:他們在基本的講法上面還是維護報禁這個政策,但區別是不露痕跡的還是明確新聞自由的這種講法。他們自己本身認不認同報禁?他們受過現代化的教育,在學校教書,當時的環境是這樣,他們公開當然要講報禁的理由,但是跟同學們私下是什么態度? 鄭:在我的印象中,私下很少談這么敏感的問題,畢竟環境不一樣,他們也是要慎重,但是后來特別是王洪鈞老師從美國回來,他就比前面幾位老師講得更多。王洪鈞寫的**篇文章結果引起軒然大波,叫作《如何使青年接上這一棒》,那時候很多上一代的老人家怪他:你在鼓動青年搶飯碗。 蘇:他是有理想性的人。 鄭:你去看一看他們過去的文章,不止是對新聞自由的問題,就是對整個“國家”的走向,他們都還是非常有理想的,而且敢講話。王洪鈞是受到胡適之的影響,他做記者時經常訪問胡適之,非常有理想。徐佳士老師是**個翻譯西方大眾傳播理論的學者,他寫的那本《大眾傳播理論》風靡一時,非常深入淺出。這種傳播理論里面啟發我們人類傳播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蘇:也讓我們反思我們所處的社會環境到底是什么樣子的。就像您剛才講的自由和控制是中性的名詞,尤其是在大學院校里面看到報禁,其實也是一個中性的名稱,應該是用這種態度去看。 鄭:對,我覺得應該是這樣。 從“蔣公的人”走向“專家”時代 蘇:您當時在中央文工會擔任副主任,您擔任副主任那個階段還是報禁時期,當局在具體的管控媒體的方式和手段方面有哪些? 鄭:我的印象就是我在文工會負責的時候,其實這種演變已經慢慢開始了,過去的宣傳主體,像宣傳部長、副部長基本都是“總統”*信任的、過去在新聞界任職的人士,而且還有一個很有趣的特色,他們幾乎都是從哪里來的?秦孝儀、楚崧秋、宋楚瑜,這些人都是新聞秘書出身,他們都是深得蔣公信任的人,專門派他們出來做黨營媒體的社長或負責人。我是那個年代在李登輝任內任命的**批,我在蔣經國時期在青工會是專任委員兼總干事。我在青工會11年,后來才到文工會,從青工會調到文工會的時候我不是李登輝派任的,是李煥派任的。其實客觀地講,從那個時候開始,對宣傳部主管人員的任命開始走向“專家”時代。我一直都是學新聞、教新聞的,不是過去傳統那種在“總統”身邊做新聞秘書多少年然后任命的人士。我個人的體會是過去文工會對媒體的控制非常厲害,不過報禁還沒有解除時,我們對于媒體的管制已經逐步放松了。 說到管控手段和方法還是有好幾種:**個,媒體主要還是黨營媒體較多,有八大黨營媒體,如中央社、《中央日報》、《中華日報》、“中視”、“中影”等等,而《聯合報》、《中國時報》都是后來發展起來的。所以**個很簡單,就是人治派任,用人治來控制。你看那時候,文工會的副主任都是“中視”總經理,總干事起碼也是個副社長。 第二個,新聞協調。重要的事情,文工會約請重要的媒體負責人,咨詢新聞界該如何處理?當然他也會邀請很多人做背景調研,關于外交敏感的問題請“外交部長”講為什么“中美斷交”了,背景是什么樣的,媒體該怎么把握言論。 第三個,政策傳達。黨目前對某件重要的事情有什么重要的政策,他要跟這些媒體人士傳達,他們回去寫社論,配合新聞報道。特別重要的事情,如果沒有時間開這種會,比如突發了一個重要事件,通常是電話通知,所以為什么說那個時候總干事不得了,指令就像圣旨一樣的,一個總干事打一個電話,總經理、副總經理或者新聞部經理都得按照他的意圖去辦。 還有一種,那個時候我的理解文工會是真正黨的宣傳工作方面的主角,“新聞局”其實只是在舞臺上表演的。我還記得,那時我是文工會副主任,管新聞這一部分,邵玉銘在“新聞局”做“副局長”,我們常常碰到,我等于是在傳達黨中央的聲音,由他們“新聞局”去計劃、執行。但是,事前他們要到文工會來了解,我們曾經一起開過無數次會議。 文工會下面分好幾個室,一是管新聞聯系的,二是管地方宣傳的,三是管文學藝術的,四是管新聞媒體的等等。每一個室都有不同的任務、不同的角色,碰到特定重大事件,比如和美國很緊張的時候,這一段時間的新聞每天都要注意,每天都要了解,特別是黨能夠管到的那幾個方面更是要重視。 蘇:請問在報禁時期,當時的政治領袖對各個媒體有些什么影響或者作為? 鄭:那個時候在公權力機關這一部分,包括我們在內,當時很期盼公權力機關做公共關系,那時候的“交通部部長”賀衷寒先生推動很多公關工作,公關界有很多人稱賀衷寒為“公關之父”。我在文化大學,創辦公共關系專業,臺灣**個廣告系是我辦的。我們開始認識到政府公共關系的重要性,包括我們也常常和“新聞局”合作,“新聞局”主辦公關人員的訓練班,中間一定會邀請了解中央政策的人去講。“新聞局”講的大部分是公關技術,我們那邊主要傾向于公關政策方面。 所以在政治領袖里面,經國先生據我了解對于新聞界是很接納的,還是蠻寬容的。我也兼任過英文《中國郵報》副社長,余夢燕做社長,她是報界女強人。期間蔣經國先生就召見過幾十位重要媒體的主管,我也去了,蔣先生他也問了很多新聞界對“國家”大事的看法。我還和黃遹霈、余夢燕夫婦去和蔣經國先生談,據我了解他接見《中國郵報》不一定公開,外面不一定都知道,他也很重視、很尊重新聞界的意見。 當局官員里面有幾個人是對新聞操作比較有興趣的,或者對這方面比較有他的想法,或者說有他的野心的。謝然之老師后來為什么被派出做“駐外大使”?就是被排除出去了。因為那個時候中央黨部有兩個副秘書長秦孝儀和謝然之,他們兩個人的專才不一樣,興趣也不一樣。秦孝儀對新聞界、新聞媒體非常有貢獻、非常重視。他和謝然之二人想涉入的領域也不一樣,因為秦孝儀兼做蔣公的新聞秘書,天天在蔣公面前咬耳朵,所以后來把謝然之派出去了,避免他們兩個人之間的紛爭。宋楚瑜當然對新聞媒體這一塊軟的、硬的用了很多方法,在新聞或宣傳這一塊,特別是對文工會的影響力還是較大的。 蘇:您曾經在《中央日報》和中央通訊社實習過,當時情況如何? 鄭:我大學三年級就開始在《中央日報》。那時候《中央日報》一天只出一大張報,我在報社做正式的助理編輯。你知道我什么時候去上班嗎?那是我一輩子*辛苦的一段日子,晚上12點上班,上到天亮,做國際航空版的助理編輯。《中央日報》國際航空版是專門銷到海外的,給留學生、海外華僑看。要等到“國內版”編完了,才開始編輯“國際版”,所以我都是12點去上班,“國內版”的編輯都下班了,我們開始編輯。那是我*辛苦的時候,后來就一直在研究所念完書,我畢業出來跑黨政新聞,也跑“行政院”和“內政部”(連震東那時候是“內政部長”),他們很重視《中央日報》,《中央日報》替他們寫的東西和報道跟他們很親近,采訪機會也很容易,那時候《中央日報》記者出去采訪人家非常歡迎。 時代在變,潮流也在變 蘇:您認為是什么促成了報禁開放?請列舉具有代表性的事件和人物? 鄭:基本上一方面是國際的壓力,一方面是島內的壓力。國際壓力方面國際輿論對我們十分的不利,不能否認臺灣那幾年經濟發展做得不錯,政治是專制獨裁,還實施黨禁報禁,國際上特別是美國經常給臺灣形成相當大的壓力;島內的壓力更大也更近,反對運動主要就是針對這些議題,這也是為什么蔣經國會說“時代在變,潮流也在變”。 那時候的秘書長應該還算是保守中的開明派,包括李煥先生,他對新聞界也很同情、很了解,所以他們都有不露痕跡的把海內外的形勢給經國先生報告,經國先生也是耳聽八方,他也是多方面的聽取意見,中間當然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錢復先生,他在做“駐美代表”的時候,經常把這種“國家”壓力、國際輿論反映到經國先生那里,他跟經國先生可以直接講話,把這種狀況直接轉告給經國先生,包括黨禁年代的“戒嚴法”,他曾經說:我們真正實行的“戒嚴法”只有西方國家定義的百分之多少? 蘇:百分之三,我記得是這樣,我們叫“百分之三的戒嚴”。 鄭:是的,我們要去抗整個這樣一個壓力,實在不劃算。當然這件事情真正暴露出來,是《華盛頓郵報》的社長Graham(Katharine Graham凱瑟琳·葛蘭姆)女士到臺灣來,蔣經國接受了她的獨家訪問,錢復與當時的“新聞局局長”張京育負責安排Graham女士的專訪。Graham對臺灣印象一直不好,《華盛頓郵報》對臺灣的態度一直也是不友好、批評的。 蘇:您剛提到美國、錢復、美國態度和壓力等情況,請問美國那時候的盤算是怎樣的?他們對臺灣報禁問題的著眼點是什么? 鄭:我覺得不一定判斷準確,美國這個國家是要向世界推銷他的法寶,要你改造成像他一樣的國家,你光是經濟發展很好但還是獨裁,他們就很不滿,他們對老蔣從誤會到慢慢接受,這中間也經過一個過程,他并不是那么熱心在支持你,這也是不得已的選擇,所以我相信他還是為美國的理想和利益。我曾經指導過一篇博士論文《杰斐遜托馬斯·杰斐遜(Thomas Jefferson)。新聞思想的研究》,我到杰斐遜紀念塔去過兩次,我收集了杰斐遜的很多資料,他的觀點也普遍為美國人所接受,確實有那樣的總統,也不完全說是自私的。所以,理想、現實壓力、“國家”或個人利益等因素都有。 蘇:您認為臺灣媒體在民主轉型的過程當中扮演了什么樣的角色? 鄭:絕對是正面而且非常重要的,過了頭的這一部分也不能說完全沒有,我對馬英九印象不好,我也覺得現在有點過了頭了。所以,臺灣報禁解除對于臺灣民主政治深有影響,民主運動畢竟是全民運動,每一個人民都要有這樣的參與才會是真民主。媒體在平常所灌輸的自由民主思想慢慢深入到民間,深入到老百姓的心中,培養人民的人格基礎。 這次我去廈門大學參加一個學術會,大陸、臺灣、香港有幾十位學者參加,*后我做閉幕總結發言,我說媒體界也好、行政部門也好,必須知道在媒體角色變化的情況下,尤其是互聯網時代,需要注意三點:過去我們社會的基礎是建立在三個基礎上,一是權力者,有權的人,特別是皇帝高高在上;第二是貴族階級,封疆割土,各霸一方;第三個是哲人,就是讀書人、知識分子,中國人為什么要拼命讀書?是要成為一個讀書人。除了這三種人之外,你在這個社會上一輩子不得翻身,你生來什么角色一輩子就是那個角色,甚至于世世代代永世不得翻身,但這三種人畢竟是很少很少的,在人口中所占比例太少。 今天的社會結構面臨一個新時代的到來,臺灣社會的結構組織(我相信臺灣還很少人講這兒)也是三大基礎:**就是個人的自尊,每個人都很有自尊,任何一個人都不能隨便侵犯他的權益;第二是彼此的同情,特別是對于弱勢群體的同情,就馬英九和王金平的“關說”事情來說,王金平也有錯,但是為什么大家不敢明講,很多的老百姓覺得馬英九在欺負人家,過度的強逼,不顧人情。我并不是說王金平沒錯,但是我更不同意馬英九用這么強勢的手段。再比如*近洪仲丘事件,一個阿兵哥,二十幾萬民眾上街支持。所以一個文明現代社會的標桿,就是看這個社會對弱勢族群采取什么態度,新女權運動、同性戀者等等,現在我們對待這些跟過去相比有很大的轉變,你不要小看小老百姓,他利用網絡一通知,馬上二十萬人上街支持,他又不是為權力為個人,他就是有一種同情心,現代社會集思廣益大眾的智慧,來發掘*好的解決方法。 新聞自由是誰的自由? 蘇:請談談解禁后,臺灣媒體與當局之間關系有些什么變化? 鄭:當然有變化,輿論界因為在報禁之后獲得更多的自由空間,對當局的監督和批評更多了,更自由了,更全面了。當局變得有點像個小媳婦,我覺得他們非常左右兩難,又不能不尊重新聞界,但是新聞界的批評又不一定全部都是真正客觀的,我個人覺得有時候有點過。過去是不夠,現在有一部分媒體有點過。主要是新聞工作人員的專業知識和對問題的了解不夠深入,現在很多的記者都很年輕,特別是主持有點深度的節目的或者寫專欄的,需要對背景有詳細的了解,所以在分析問題和觀察問題的時候就沒有辦法真正的調查和分析。 加上現在民主的流弊,民主有正反兩面,正面的就是針對信息管道的公開,確實也是對當局的某些不當措施有一種預警,但是也不是沒有偏見的,比如某臺它是民進黨的,那么無論如何都認為民進黨是對的,或者某臺是當局的,那么當局的就都是對的,這有失輿論真正的理想。 當然,我們有點理想化,學院派都難免有些理想化了。所以我覺得有時候會牽扯到專業教育。我做大眾傳播教育協會秘書長的時候,9個院校有新聞傳播系,現在有120多個學校有新聞與傳播系,新聞傳播很時髦,年輕人喜歡,很好招生,但里面的師資、設備特別是辦校的重心都有點問題。
野火之后-當代臺灣新聞業觀察.反思與批判 作者簡介
向芬,博士,副研究員。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新聞學研究室副主任,中國新聞史學會常務理事。研究領域為新聞傳播史論、新聞傳播制度與管理政策。
- >
姑媽的寶刀
- >
上帝之肋:男人的真實旅程
- >
自卑與超越
- >
我從未如此眷戀人間
- >
回憶愛瑪儂
- >
唐代進士錄
- >
小考拉的故事-套裝共3冊
- >
朝聞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