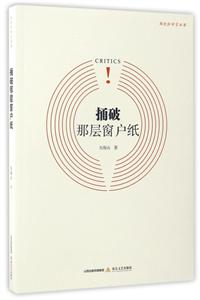-
>
百年孤獨(2025版)
-
>
易中天“品讀中國”系列(珍藏版全四冊)
-
>
心歸何處
-
>
(精裝)羅馬三巨頭
-
>
野菊花
-
>
梁啟超家書
-
>
我的父親母親:民國大家筆下的父母
捅破那層窗戶紙 版權信息
- ISBN:9787537850315
- 條形碼:9787537850315 ; 978-7-5378-5031-5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捅破那層窗戶紙 本書特色
《捅破那層窗戶紙》是針對現代文學和文化的評論。無論涉及到余光中、龍應臺、王朔、嚴歌苓、南懷瑾、閻崇年、余秋雨等當今文壇的大家,還是事,還是事件,作者關海山皆一視同仁,知無不言,劍走偏鋒,一吐為快。作者思想深刻,文字幽默,能從眾人視而不見的角度入手,一針見血,痛快淋漓,既有嚴肅的學術性,又有時尚的可讀性。
捅破那層窗戶紙 內容簡介
山西文學有著深厚的傳統,山西的文藝理論與評論在中國文藝批評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進入當代,山西的文學理論與評論仍然保持了比較活躍的態勢。特別是新時期以來,可謂陣容強大。新一批評論家涌現出來,他們知識結構新穎,對新現象、新趨勢特別敏感,個性色彩極強,表現出活色生香的發展態勢。 《捅破那層窗戶紙/新銳批評家叢書》就是山西文學評論家關海山所著的一本文學研究和評論合集,共收文97篇,包括《注定夭折的“龍卷風”》、《也說金庸訴江南侵權案》、《所有的花你*美》等。
捅破那層窗戶紙 目錄
注定夭折的“龍卷風”
王朔走進了“千歲寒”
陶醉在臆想的世界中——從《拯救乳房》和《血玲瓏》看畢淑敏的小說創作
這些常識應該懂
讀不懂的《小東西》
不敢再讀“格林童話”
培育邪惡的溫床
劉亮程:別再糟踐這村莊了
糟踐完村莊糟踐新疆——評劉亮程散文集《在新疆》
矯情的“不為影視寫作”
誰解新版《紅樓夢》之味
也說金庸訴江南侵權案
娛樂節目要狠剎媚俗風
讓更多的作家介入編劇
武將形象該如何
主旋律影視也要血肉豐盈
為易中天、于丹說句公道話
關鍵的問題是治本
影視劇要彰顯文化品格
為文藝作品作者正名
所有的花你*美
文藝作品的思想和道德
從平淡中過濾生活——電視連續劇《懸崖》瑣談
國產動漫期待跨越
遭人非議的“行為藝術”
從《潛伏》到《借槍》
我讀外國小說之惑
故弄玄虛的禪語
從出口成章說起
低齡寫作不應鼓勵
兒童需要什么樣的文學
批評何須有鋒芒
語言問題不可忽視
“丟書大作戰”可以止矣
漢字中不應夾雜外文
由漢語與西文字母之爭想到的
漢字簡化是文字發展的方向
令人堪憂的網絡語言
寫首兒歌給孩子
作家應該成為多面手
取筆名要有尺度
酷評更是有思想的生產
朝氣蓬勃的“媒體派批評”
白平:是又怎么樣
網絡文學的癥結
由余秋雨引發的思考
忌散貴散說散文
文學批評惹誰了
文學評論的三大頑癥
文學評論的是與非
文學評論貴在批評
也談“80后”的寫作
毀譽參半的網絡文學
文學命名應謹慎
散文到底該寫什么
散文的園地應該大起來
是翻譯不是篡改
陷入怪圈的《紅樓夢》研究
別總拿“隱私”說事
裸體與閱讀
有所讀有所不讀
“作者簡介”里的學問
“腰封”漸欲迷人眼
《收獲》并不是一桿秤
讀書要會讀
還是要讀些“無用”書
讀書與素養
由《焚書指南》說開去
39萬元人民幣的價值
《獨唱團》攪皺了文壇“春水”
數字出版應再規范些
圖書也是商品
莫言獲獎引起的話題
“文化名人”不等于“國學大師”
拜年不是走形式
過年過什么
漢字不能僅限于聽寫
取名字能不能用生僻字
傳承方言就是傳承文化
惡搞文化何時休
文字是文明的基石
紅色旅游景點應該免費開放
保留老地名就是保存文化
鶯鶯塔當“嫁”則“嫁”
有感于名人當教授
作家掙錢引出的話題
歌詞為什么寫得那么爛
我們還需不需要詩歌
別讓詩歌沾染上“口水”
“讀不懂”不是不讀詩的理由
新詩要力戒散文化
新詩要不要押韻
詩人到底會不會說人話
新詩何求要能“歌”
古典詩詞創作的當下意義
女詩人的胸部與詩歌沒有關系
捅破那層窗戶紙 節選
《捅破那層窗戶紙/新銳批評家叢書》: 中國有句話,叫“文如其人”。當然,我們也不能要求作家們都要公而忘私或舍身飼虎去,但起碼的平等、尊重等禮儀常識總該具備的。從余光中的文章里,我卻分明看到了一顆骯臟的靈魂,這顆骯臟的靈魂是受其丑陋的思想意識支配著的。如在游記《塔阿爾湖》中,余光中在盛贊菲律賓女人“褐中帶黑,深而不暗,沃而不膩,細得有點反光的皮膚”的同時,卻又用無限厭惡的筆調去描繪:“比起這種豐富而強調的深棕色,白種女人的那種白皙反而有點做作,貧血,浮泛,平淡,且帶點戶內的沉悶感。”就像“你不能選擇自己的出生,卻可以選擇自己的人生道路”一樣,膚色本天成,無論黑、黃、白、棕,你有什么理由更有什么資格去嘲笑與侮辱你所看不慣而別人又無能為力去改變的膚色呢?尤其可惡的是,在游覽一座“眾鬼寂寂”的古寺時,愿意保持安靜的余光中,竟然斯文掃地地謾罵為他辛苦奔走的向導:“岑寂中,只聽得那該死的向導,無禮加上無知,在空廳堂上指東點西,制造合法的噪音。”接著,又惡毒地詛咒:“十個向導,有九個進不了天國!”(《不朽,是一塊頑石》)你余光中先生倒是有禮又有知,卻為何要面對因養家糊口而為你服務的可憐向導大發雷霆呢?僅僅因其為了討好你而攪了你的雅興便值得如此大動肝火嗎?若如此,像余光中先生這樣的“知”和“禮”,還是不要也罷!再就是,在《論夭亡》一文中,余光中先生“歪理加邪說”地證明了夭亡的諸多好處后,又不厭其煩地舉例雪萊的天亡與佛洛斯特的老死,*后競得出結論:“死亡不但決定死,也決定生的形象;而夭亡,究竟是幸,是不幸,或是不幸中之大幸,恐怕不是常人所能決定的吧?”真是扯淡!死亡就是死亡,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怎么夭亡就比正常的老死“大幸”呢?與此有同工之妙的,恐怕也就“作法不自斃,悠然過四十”的錢玄同了。稍微“遺憾”的是,錢先生的觀點對世人所產生的毒害與余先生比起來,可就小巫見大巫了。 當然,余光中先生畢竟是作家,我們也不能老揪住人家的道德情操不放手,何況歷史上人品不怎么樣而才高八斗者也大有人在,比如和坤,比如秦檜。我們也還是從文學的角度去認識認識余先生吧。 余先生*得意*炫耀的文學觀點便是“煉丹”,在其《逍遙游》的后記里余先生不無自負地說:“我倒當真想在中國文字的風火爐中,煉出一顆丹來……我嘗試把中國文字壓縮、捶扁、拉長、磨利,把它拆開又并攏,折來疊去,為了試驗它的速度、密度和彈性。”且不說這話里用了多少無聊的比喻、夸張等修辭手法,我們只看余先生是如何在自己的文字里煉丹的。 余先生首先煉出了一顆文白夾糅、歧義叢生、晦澀難懂的半生不熟的青瓜“丹”來:“我的觀星,信且所之,純然是無為的。兩睫交瞬之頃,一瞥往返大干,御風而行,冷然善也,冷然善也。”這樣半古不白的文字,即使20世紀30年代那一茬剛學白話文的作家,也要比他運用得圓潤得多,稍有點古文基礎的人,都能讀出這幾句話的生硬與別扭來。但余先生卻不會這樣認為,“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是余先生慣用的伎倆,盡管余先生自己樂此不疲地寫著不文不白的夾生文章,卻還要蔑視“五四或30年代(上世紀——引者注)的名家,那種白話文體大半未脫早期的生澀和稚拙,其尤淺白直露者,只是一種濫用虛字的‘兒化語’罷了。”(《哀中文之式微》)同樣,余先生一邊大聲嘲笑著現代刊物上如《未完成的戀曲》《生命的燈》《褪色的夢》《石榴花開的時候》等“那些沒有個性、陳腐不堪的題目”“都是老祖母時代流行的帽子了”,一邊卻鉆進書齋汗流浹背津津有味地創造著一點也不比他所舉的例子高明一丁點的《南半球的冬天》《下游的一日》《借錢的境界》《幽默的境界》《中國人在美國》等陳詞濫調——可笑啊可悲!為了增加自己文章的文化內涵,也為了顯示自己學問的廣博(或深厚)及活學活用的本事,余先生時不時要活剝些古人的詩句,“剝”得好也算,這本來無可非議,只是畫虎不成反類犬,余先生活剝的手段太不怎么高明了,剝著剝著,便剝出了一顆毛茸茸血淋淋的胚胎“丹”來:“上有青冥之長天,下有淥水之波瀾。長風破浪,云帆可濟滄海。行路難。行路難。”(《逍遙游》)“正如路是人走出來的,地址,也是人們住出來的。”如此蹩腳的活剝,實在令人惡心、令人不忍再去舉例,然而余先生卻興趣盎然,一剝再剝。在另一篇寫雨的散文里,余先生的心情毫無緣由地“則在凄楚之外,更籠上一層凄迷了”,于是,“饒你多少豪情俠氣,怕也經不起三番五次的風吹雨打。一打少年聽雨,紅燭昏沉;二打中年聽雨,客舟中,江闊云低;三打白頭聽雨在僧廬下,這便是亡宋之痛。”(《聽聽那冷雨》)猛一看,還以為余先生才華橫溢呢,不料想,還是活剝了宋人蔣捷的《虞美人》:“少年聽雨歌樓上,紅燭昏羅帳。壯年聽雨客舟中,江闊云低,斷雁叫西風。而今聽雨僧廬下,鬢已星星也。悲歡離合總無情,一任階前、點滴到天明。”對比之下,高下優劣立時一目了然。 ……
- >
史學評論
- >
新文學天穹兩巨星--魯迅與胡適/紅燭學術叢書(紅燭學術叢書)
- >
我從未如此眷戀人間
- >
企鵝口袋書系列·偉大的思想20:論自然選擇(英漢雙語)
- >
中國人在烏蘇里邊疆區:歷史與人類學概述
- >
自卑與超越
- >
唐代進士錄
- >
有舍有得是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