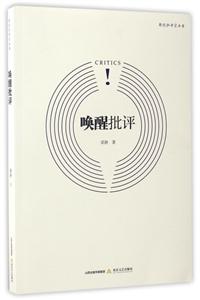-
>
百年孤獨(2025版)
-
>
易中天“品讀中國”系列(珍藏版全四冊)
-
>
心歸何處
-
>
(精裝)羅馬三巨頭
-
>
野菊花
-
>
梁啟超家書
-
>
我的父親母親:民國大家筆下的父母
喚醒批評 版權信息
- ISBN:9787537850933
- 條形碼:9787537850933 ; 978-7-5378-5093-3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shù):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喚醒批評 本書特色
《喚醒批評》為文化評論文章合集,所收文章以文學評論為主,兼有電影、攝影、時事評論。作者梁靜一直在探索如何能夠讓批評有效、如何讓批評文本獲得其藝術屬性等問題。作者在寫作中不斷叫醒、提醒自己,更清 晰、準確地深入文本去發(fā)現(xiàn)和思考,進而形成有說服力和獨立價值的 文本。
喚醒批評 內容簡介
山西文學有著深厚的傳統(tǒng),山西的文藝理論與評論在中國文藝批評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進入當代,山西的文學理論與評論仍然保持了比較活躍的態(tài)勢。特別是新時期以來,可謂陣容強大。新一批評論家涌現(xiàn)出來,他們知識結構新穎,對新現(xiàn)象、新趨勢特別敏感,個性色彩強,表現(xiàn)出活色生香的發(fā)展態(tài)勢。 《喚醒批評/新銳批評家叢書》一書就是山西文學評論家梁靜的一本文學評論集,共分三卷,文章有《我是女人,但首先是人》、《母愛之重,何以安放?》、《女性文學怎么寫史?》等55篇。
喚醒批評 目錄
在大洋彼岸哭泣的《扶桑》
有“奴隸的母親”,才有《秘密的女兒》
我是女人,但首先是人
《婦人》到底有何過人之處?
班妮是宮怨詩人,還是女權主義先驅?
侯虹斌,一個主動在寫的女作家
夫貴妻榮對女性來說有用嗎?
問題少女的愛情一定就得是悲劇?
只有性話語才能顛覆男性敘事中心?
“州官放火”的世界,小女子“點燈”無妨?
有一種青春文學叫笛安
為什么說《東霓》超越了《西決》?
菩提樹下的精神樂果
我看韓寒
李駿虎印象記
《水滸》怎么新說?
《小春秋》里的大智慧
《教授》是一把隨時扣動扳機的槍
真愛的唯一版本是《非誠勿擾》?
支撐基層女作家文學夢的是什么?
一筆一筆打撈平凡
女性寫作者怎么擺脫小家子氣?
文學是一劑解救靈魂的良藥
幸福何以抵達深處?
搭上“60后”的列車看中國
王艾甫送陣亡通知書的時候在送什么?
非虛構+小說=非虛構小說?
紛飛的理想中現(xiàn)實并不骨感
卷二
母愛之重,何以安放?
和魔鬼爭奪未來的“人類之光”
大屠殺之后的盧旺達還需要上帝嗎?
小說還能跑過影視劇嗎?
有一種女性叫性工作者
《失蹤女人》丟給知識分子一個問號
《金婚》的生育觀還不夠荒謬?
《螞蟻》的歸《螞蟻》,賈樟柯的歸賈樟柯
歪歪扭扭的路上我們在狂奔
和坤聰明嗎?
能進入攝影史靠的是什么?
攝影與文學,融合是可能的嗎?
能讓人讀懂的攝影就是好攝影?
攝影批評能否助推攝影市場化?
攝影批評需要更多介入
在大公和私欲之間隔著什么?
《孝義千秋》,自我追求與超越的結晶
皮影進入學術研究領域的扛鼎之作
女性的被損害仍然是這個時代的痼疾
卷三
易中天先生的“瓦錐”里包括女人嗎?
尊重女權就是尊重人權
女性文學怎么寫史?
上墳這事和女性有關系嗎?
誰說賢妻良母就是好女性?
學會尊重女性就那么難嗎?
鐵飯碗男少女多,因為機械執(zhí)行“不得有性別歧視”?
批評是一門手藝活兒
附錄一 女性主義的講述 張銳鋒
附錄二 大情懷:女性主義者的視界與精神 馬明高
附錄三 梁靜:女性世界里的精彩跨越 武凌霄
后記
喚醒批評 節(jié)選
《喚醒批評/新銳批評家叢書》: 我們很難不把烏莎同中國的國情結合起來思考,因為我能隨手拈來自己身邊的烏莎,這些烏莎顯然和小說中的烏莎一樣,雖然不至于出生就被殺死,多半也是家里多余的不想要的分子,雖然她們的父母也會不忍和不舍,但比起他們偏好男孩的性別取向和不可理喻的義正詞嚴,處理掉一個女孩這種貌似理智的殘忍,似乎是*合情合理的一種選擇,謀殺和拋棄就在這樣一種強大的畸形的文化習俗面前得以實施了。在這一點上,印度和中國沒有太大區(qū)別,重男輕女的觀念同樣畸形地影響著中國人對待女孩的方式。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廣泛應用于民間的胎兒性別鑒定和墮胎技術,是加劇性別失衡的技術性因素。據(jù)中國新聞網(wǎng)報道,印度30年問被流產(chǎn)女嬰約1200萬,弒嬰行為并不罕見,2001到2011年之間的0—6歲兒童女男比例分別是927:1000,914:1000,十年時間,女孩比男孩減少數(shù)從600萬擴大到7lO萬,并且還在不斷擴大,這一事實已令許多印度人深感恐慌,目前印度女男整體數(shù)量比為940:1000,兩性比例嚴重不協(xié)調使印度“適婚女子匱乏讓‘租妻’生意紅火起來,無處娶妻讓‘買春’現(xiàn)象激增”,盡管如此,報道中稱:“印度兒童性別比仍然是世界上*糟的情況之一,盡管好于中國。”由此可見,中國比印度,在面對女孩的態(tài)度上,更勝一籌。中國什么情況呢,2011年人口普查統(tǒng)計結果是,男女性別比高達120:100,男女人口出生性別比為117.78:100,有關媒體就此推斷,到2020年,中國將出現(xiàn)3000萬光棍。光棍將要出現(xiàn)了,我們的男性便甚為焦慮了,于是,各種辦法出臺了,讓人感到寒心的是,目前在社會心理上反映出來的焦慮,幾乎沒有是關乎于女嬰擁有的生命平等權的,而是把更多的焦慮集中于可能找不到老婆、娶不到媳婦的光棍們的身上。先不說以后,只說眼下,120:100的男女比例所催生的社會問題同樣令人深思,與印度無二。2012年2月21日,央視12頻道播出了一檔節(jié)目,主要內容是破獲了一起70余人發(fā)卡的組織賣淫團伙,70余人中,2人為頭目,66人為發(fā)卡人員,3人為制卡人員和司機,無論從判決人數(shù)統(tǒng)計上看,還是從報道中女頭目的交代推斷,該團伙中從事性交易的女性比例都少于組織服務人員,大概人數(shù)在十幾名左右,而且,據(jù)辦案人員了解的情況分析,這些人都從中牟取了暴利,那么,據(jù)此推論,這個70余人的犯罪團伙,完全是被十幾個女性在養(yǎng)活著。這只是中國破獲的許多組織性交易案的其中一起,很多團伙人員都是由女性的性交易供養(yǎng)著而牟取暴利,真正從事性交易的女性其實賺取得并不多,她們付出肉身的結果只為了生存,她們的勞動果實卻被一層層榨取了。這種現(xiàn)象與印度“無處娶妻讓‘買春’現(xiàn)象激增”無本質區(qū)別,小說《秘密的女兒》中,同樣有所揭露,比如希爾皮在“兩個印度”一節(jié)中寫到的一些家庭中的女性通過長期做妓女供養(yǎng)家庭,就如同清末民初北京胡同里的暗門子。印度“租妻”現(xiàn)象的火爆,讓我想起了柔石的《為了奴隸的母親》,這些被租出去的妻子,不正是那“奴隸的母親”的再版嗎?中國出現(xiàn)的什么借腹生子、代孕人與那“奴隸的母親”又有什么區(qū)別?再舉一例,2011年,某省臺播出一檔親情欄目,題目已記不清楚,事情由一名父親無錢救治身患重疾的兒子而決定把豆蔻年華的女兒嫁給一個五十歲老頭換取五十萬的治病費用為起因,該欄目組將這一家人請到現(xiàn)場,專家和觀眾同聚一堂來討論這件事,欄目中力阻父親嫁女兒的母親辛酸的淚水和對父親憤怒的踢打震撼了全場,愛的力量和無奈求助的哭泣讓所有專家和觀眾對該父充滿了痛恨的情緒,那位母親悲痛欲絕的形象永恒地停留在了我的腦海之中。中印現(xiàn)實和小說中的這些情節(jié),正是女性被嚴重歧視的杰作,因被歧視而引發(fā)的女性被遺棄、被收養(yǎng)、被下流、被傷害、被暴力、被殺害、被騷擾、被結婚、被妻子、被母親、被主動賣淫、被不敢辭職、被不敢生育、被主動下崗、被選擇做全職太太的這些杰作,其實仍然天天在中國大地上不斷地上演。女性既被男性無可救藥地需要著,又被男性無情無恥地踩在了腳底下,既被社會所希望地提供著廣博而深刻的作用,又被貶低和忽視著這些重要的價值,這是十分矛盾和荒誕的理論和實踐完美結合的社會建構。兩性性別比越失調,地位越低,女性被物化地就越嚴重,如果女性生存狀況和政治、經(jīng)濟權利得不到保障,地位不提升,人類社會的兩性關系就會不平衡,這種不平衡的社會建構的*終走向,必然以人類全體速亡為終結。 ……
喚醒批評 作者簡介
梁靜,筆名驍馳,山西省作協(xié)首屆簽約文學評論家,文學創(chuàng)作二級。出版有文化批評集《交叉小徑——游走于蒙昧與清醒之間》,發(fā)表評論、小說、詩歌及文化隨筆四十余萬字。
- 主題:生命體驗與文本世界的對話 ——談梁靜的文學批評 金春平
梁靜的文學批評兼及藝術批評,盡量逃避學科化的專業(yè)術語——那些或陌生或冗長或奇異的詞匯總是讓人望而生畏,更未事先設定理論框架,將藝術文本適足削履的作為印象式、模糊性乃至想象性論點的注腳;相反,她對文學文本、影視作品乃至文化現(xiàn)象的分析,總是循著觀賞者—游歷者—反芻者—超越者的心理思維邏輯,直至將批評效果編織為言說的黑洞——那種源于大眾的生活思考和文化浸淫卻又普遍難以自知的言說覺醒。無論是《在大洋彼岸哭泣的扶桑》、《有“奴隸的母親”,才有秘密的女兒》、《夫貴妻榮對女性來說有用嗎?》、還是《我是女人,但首先是人》、《婦人到底有何過人之處?》、《侯虹斌,一個主動在寫的女作家》,無論是涉及文學文本還是影視文本,梁靜的文學批評總是帶著強烈質疑和問題意識,以反叛者的姿態(tài)遵著時代語境—個人經(jīng)驗—文本呈現(xiàn)—理性思考的多元立體的思路全面涌入,這樣的批評資源和方式,在保證了批評背景具有一定的時代廣闊度和歷史縱深度的同時,更實現(xiàn)了批評家—作家(作品)的“對話”。而對話的確立,恰是批評話語獨立的標志——它摒棄了批評家自說自話和匍匐追隨的極端姿態(tài);同時,這種對話所具有的個體情感投射和心靈溫度,又讓梁靜在進行理性分析的批評實踐時,始終不失作為言說者的個人寫照,而那種純技術性乃至技巧性的分析,正是她所極力回避的。因此,當中國當代文學批評完全被理論話語和理論武器所武裝,在一個個操持著熟練的理論工具將文本作為僵尸進行生理解剖的批評氛圍中,梁靜的文學批評作為一個有著生命溫度的批評者的話語聲音,重建著作家與批評家、文本與社會、文本的虛擬世界與現(xiàn)實的生活世界的互文性參照,并在多重聲音的對話中,復現(xiàn)著梁靜作為思想者的凝望和書寫者的獨立。 其次是女權主義的價值實踐。正如韋勒克所說,文學批評需要具備文學理論與文學史的視閾融合,文學批評一定意義上是參與文學史構建的前提,但是,文學批評卻從古至今遵循著批評個體的標準進行,普遍主義的文學史也就無法構建,只能在相對主義的意義上不斷書寫著永無盡頭的文學史。梁靜文學批評的價值體系,盡管充分關注著每一部藝術文本的藝術性與真實性的處理、地域性與世界性的借鑒、思想性和審美性的融合,以此作為判斷作品水準高低的條件和標準,但是梁靜文學批評最鮮明的價值標準則是女權主義——一種混合著性別民主、個體壓抑、生命體驗的文學標準。她的文學批評對象大量關注國內外的女性作家和女性題材的文學影視作品,在批評言說當中同樣將重心置于各類女性的命運掙扎和生命疼痛,甚至在一些批評判斷中將主人公是否表現(xiàn)出女權主義和女權獨立作為作品成敗的標志。梁靜自稱對女權主義價值理論有著特殊的偏愛,同時她的這種將女權主義作為文學批評的重要標準在我看來也有可商榷之處,而“詩無達詁”某種意義上決定了給文學的高下優(yōu)劣下一個絕對公認的標準是徒勞的,但是梁靜這種對女性作家作品、女權主義批評實踐的“偏執(zhí)”背后,是她生命體驗的一種投射——她是借用對女性作家和女權主義的批評表達著她的生活經(jīng)驗和心靈探尋,這是對女權主義生成根源的遙相呼應,而非將之僅僅作為一個批評理論武器。在看似倔強的批評姿態(tài)背后,是一位有著多重生活思考經(jīng)驗的女性批評家,在混雜著消費主義、資本權威、政治桎梏的男權話語下的話語反抗與個體張揚,宣告著她不屈的人文理想和永不磨滅的向往自由的靈魂悸動,我想只有從這個角度進入,才能理解梁靜對女權主義的偏愛為何如此執(zhí)著與決絕。 再次是批評文體的自由跨界。作家與批評家的對立由來已久,分歧的焦點在于作家似乎以創(chuàng)造性而傲居,批評家的言說一度成為過度闡釋和亦步亦趨的代言;而批評家往往站立于文學版圖上指點江山,作家引以為榮的原創(chuàng)性經(jīng)驗,在批評家看來早已在別處被反復演繹成為濫觴。對立之后各自的審視與反思,似乎在妥協(xié)中達成了一些基本的共識,那就是文學文本創(chuàng)作與批評文本創(chuàng)作,是思想和經(jīng)驗、感性和理性、邏輯和審美等的不同表達方式,唯有打破這種對立,才是對話開啟的前提,因此,批評家率先開始了打破彼此隔閡的努力并一直未曾間斷,梁靜的文學批評文體就是這種努力的典型案例。梁靜批評文本的自由跨界,有著文化散文的理性與思索、史料與縱論,也有抒情散文的自白與宣言、感悟與情緒,既有著小說敘事的策略與技巧,也有著理論剖析的客觀與冷酷。梁靜是將批評文本作為一種獨特的美學作品在進行創(chuàng)作,而她作為批評主體的在場,讓其扮演著批評文本空間的引路人,讓閱讀者在自由漫行和駐足觀望中,尋找著文學世界隱藏的密匙,打開一幅幅奇異詭譎的景觀之門。無論這種文本景觀的旅行是長途跋涉還是短途觀光,“完整性”成為她進行文本批評的一種整體思維(與此相對應的則是學術論文圍繞某一問題進行深入探索而不及其余)——批評文本的高度濃縮的信息、精湛明了的評論、貼切恰當?shù)淖糇C、飽滿充沛的激情,都使梁靜的批評文本具有了散文的詩意和論辯的理性,在可讀、深度、廣度方面達到了一定程度的深度融合,也成就了其獨特的批評文體和風格,梁靜找到了一條屬于自己風格的批評空間,并且充滿著無數(shù)的可能和方向,我們期待著她能將這條路走到極致的完美!
- >
回憶愛瑪儂
- >
【精裝繪本】畫給孩子的中國神話
- >
隨園食單
- >
大紅狗在馬戲團-大紅狗克里弗-助人
- >
苦雨齋序跋文-周作人自編集
- >
莉莉和章魚
- >
伯納黛特,你要去哪(2021新版)
- >
我與地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