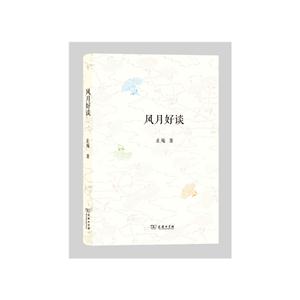-
>
百年孤獨(2025版)
-
>
易中天“品讀中國”系列(珍藏版全四冊)
-
>
心歸何處
-
>
(精裝)羅馬三巨頭
-
>
野菊花
-
>
梁啟超家書
-
>
我的父親母親:民國大家筆下的父母
風月好談 本書特色
著名傳記與隨筆作家止庵*新隨筆結集。周作人、魯迅、張愛玲、日本文學、推理小說、古拉格……涉筆之處,無不細致周到。 無關風月,洗練文字別生意趣;不飾抒情,蘊藉筆法自有態度。
風月好談 內容簡介
《風月好談》延續作者一貫文字風格,收入其近期的文化隨筆和閱讀札記,包含對魯迅、周作人閱讀和研究的一些心得,也包括對偵探推理小說、“古拉格”等歷史文學寫作文學、外國文學出版引進等方面的札記。書名“風月好談”取自作者收藏的一張日本著名作家川端康成的手書帖,用作書名,迂回蘊藉的體現了一種作者的風雅旨趣。止庵先生閱讀研究深入而細致,文風洗練,本書除對周氏兄弟、歷史寫作等具體話題有相當深入的梳理可為專業讀者提供豐富的細節信息之外,作為一般性的文化隨筆與閱讀札記,作者的文字不飾抒情,不做高談闊論,從具體話題入手,細節處略作生發對相關人物、作品和歷史文化命題自有其態度,也有較高的可讀性,可為大眾讀者提供深入閱讀的樣本。
風月好談風月好談 前言
后記
收在這本書里的文章差不多是與《惜別》同時寫的,區別在于其一講自己的事,其一講別人的事,雖然講別人的事也需要夾雜些自己的東西,譬如眼光心得之類。此外還有一點一致之處,即自己的事并不是什么都講,凡是認為無須或不宜說與別人聽的,抑或尚且沒有想好該如何說與別人聽的,我就都給省略了;議論別人時,也是將心比心,并不要求他什么都拿出來供外人去談。此之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忽然扯到這個話頭似乎有點無端,我是在雜志上偶爾讀到一篇題為“陸小曼何故如此——校讀她的兩種版本日記”的文章之后略有所感。作者對比陸小曼生前出版的《愛眉小扎》(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一九三六年)中的“小曼日記”與身后別人印行的《陸小曼未刊日記墨跡》(三晉出版社,二○○九年),發現當初她對自己的日記多有增刪改動,為此頗致不滿:“學人流傳一個說法,讀傳記不如讀年譜,讀年譜不如讀書信,讀書信不如讀日記。可見對日記真實性的期許。名人日記,一經公諸社會,便具文獻性,影響深遠,出版者應該自覺地負起歷史責任感。不然,只可混淆一時,豈得久遠。縱然遂了眼前心意,代價是失卻了誠信度,大大得不償失。近年來,出版的日記越來越多,倘若忽略本真原則,其遺患怎敢想象。”我當然很明白研究者的心思,但好像更理解陸小曼的做法:出自自家之手的文字,為什么不能修訂一下,哪怕改得面目全非。魯迅出版他與景宋(許廣平)的通信集《兩地書》,不是也有增刪改動么。作者自具權利,是非在所不論。
進一步說,日記和書信即便原封不動,也未必一定就是百分之百的真實。印行《兩地書》的同一家出版社后來出了《周作人書信》,周作人在“序信”中所說“這原不是情書,不會有什么好看的”,被認為是針對《兩地書》而言;他另外寫過一篇《情書寫法》,其中引一個犯人的話說:“普通情書常常寫言過其實的肉麻話,不如此寫不能有力量。”對此周氏有云,“**,這使人知道怎么寫情書。”“第二,這又使人知道怎么看情書。”這副眼光其實可以移來審視所有寫給別人或寫給自己看的東西。說來我對“讀傳記不如讀年譜,讀年譜不如讀書信,讀書信不如讀日記”一向有所置疑,天下事都是相對而言,并沒有那么絕對。
川端康成曾為一九四八年五月至一九五四年四月新潮社出版的十六卷『川端康成全集』的每一卷撰寫后記,講述自己的創作歷程,內容多取自當年的日記。川端說:“自從寫了之后我記得從來沒有重讀過這些日記。沒有讀卻也沒有扔掉。三十多年僅僅是帶著它而已。因為編輯全集重新讀了一遍,隨后它就將被付之一炬。”我聯想到陸小曼,她只不過沒有如同川端那般做法,結果就使研究者擁有了可供“校讀”的材料;假如早早把日記燒了,反倒不會受這一通指責。“陸小曼何故如此”——大概同樣可以拿這題目另寫一篇文章。其間孰對孰錯實在難以說清,反正我不太贊同一味強調“文獻性”、“歷史責任感”云云而不顧及人之常情。
二○一五年四月十四日
風月好談 目錄
魯迅一九三六年欲赴日療養事
魯迅與蕗谷虹兒
關于周作人
記新發現的周作人希臘神話譯稿
談編注之事
夏志清的未竟之功
“時代錯迕則事必偽”
關于一部警世之作
古拉格與底線
小津講如何拍電影
帶一本書去小津住過的房間
“我,艾米莉·勃朗特……”
我讀東野圭吾
寫在一份目錄邊上
書話是什么
關于惜別
藏周著日譯本記
日印中文書
日本旅行瑣談
后記
風月好談 節選
《風月好談》:
魯迅一九三六年欲赴日療養事
現在來講這件事情,其實是舊話重提。十幾年前,周海嬰在回憶錄《魯迅與我七十年》中對魯迅的死因提出質疑,由此引發了一場爭論,迄今為止仍未平息,而且已被列為“魯迅生平疑案”之一。這里只就其中所涉及的一個環節稍作梳理。說來并無新鮮材料,均見載于《魯迅全集》。然《全集》雖非稀見,有些發議論、抒感慨的人卻好像不大查閱。魯迅身后,大家針對他說了太多的話,眾聲喧囂之中,也許應該聽聽當初魯迅自己對此如何說法。
《魯迅與我七十年》有云:“叔叔(按指周建人)接著說:……記得須藤醫生曾代表日本方面邀請魯迅到日本去治療,遭到魯迅斷然拒絕,說:‘日本我是不去的!’是否由此而引起日本某個方面做出什么決定呢?再聯系到魯迅病重時,迫不及待地要搬到法租界住,甚至對我講,你尋妥看過即可,這里邊更大有值得懷疑之處。也許魯迅有了什么預感,但理由始終不曾透露。我為租屋還代刻了一個化名圖章。這件事距他逝世很近,由于病情發展很快,終于沒有搬成。”
王元化為此書所作序文則云:“須藤醫生曾建議魯迅到日本去治療,魯迅拒絕了。日本就此知道了魯迅的態度,要謀害他是有可能的。像這樣一件重大懸案,至今為止,沒有人去認真調查研究,真令人扼腕。”
不如先來“認真調查研究”一下《魯迅全集》。我用的是一九八一年版,面世于周海嬰著書、王元化作序之前,二位容或讀到。據周海嬰《一樁解不開的心結須藤醫生在魯迅重病期問究竟做了些什么?》一文,周建人說那番話是在一九六九年冬,《魯迅全集》出版時,他還健在。
一九三六年六月二十五日,許廣平致曹白信(注明“由魯迅擬稿,許廣平抄寄”)云:“至于轉地療養,就是須藤先生主張的,但在國內,還是國外,卻尚未談到,因為這還不是目前的事。”此乃魯迅首次提及“轉地療養”,的確出自須藤的建議,但顯然并未指定日本。魯迅自本年“三月初罹病后,本未復原,上月中旬又因不慎招涼,終至大病,臥不能興者匝月,其間數日,頗虞淹忽”(六月十九日致邵文熔),六月六日起連日記都停筆了,至三十日才又續記。所以說“這還不是目前的事”。
七月六日,魯迅致曹靖華:“本月二十左右,想離開上海三個月,九月再來。去的地方大概是日本,但未定實。至于到西湖去云云,那純粹是謠言。”這里首次提及出行時間,也首次提及要去日本,但距致曹白信已有十余日,當是經過了一番考慮;但講“大概”、“但未定實”,說明還在考慮之中。
七月十一日,魯迅致王冶秋:“醫生說要轉地療養。……青島本好,但地方小,容易為人認識,不相宜;煙臺則每日氣候變化太多,也不好。現在在想到日本去,但能否上陸,也未可必,故總而言之:還沒有定。現在略不小心,就發熱,還不能離開醫生,所以恐怕總要到本月底才可以旅行,于九月底或十月中回滬。地點我想*好是長崎,因為總算國外,而知道我的人少,可以安靜些。離東京近,就不好。剩下的問題就是能否上陸。那時再看罷。”至此就很清楚了:去日本,乃是魯迅自己比較若干可能的去處之后所作出的決定——旨在安靜養病,不受打擾。仍講“還沒有定”,卻已與先前意思有所不同,現在所顧慮的主要是入境問題。然而因為病情緣故,致使行期由“本月二十左右”推遲到“本月底”了。
七月十二日,魯迅日記云:“下午須藤先生來診并注射訖。”治療暫告一段落。但十五日日記即云:“九時熱三十八度五分。”同日致曹自信(注明“魯迅口述,許廣平代筆”)云:“注射于十二日完結,據醫生說:結果頗好。但如果疲勞一點,卻仍舊發熱,這是病弱之后,我自己不善于靜養的原故,大約總會漸漸地好起來的。”十六日日記:“下午須藤先生來診并再注射。”魯迅再次陷入“還不能離開醫生”的境況。十七日,魯迅致許壽裳:“弟病雖似向愈,而熱尚時起時伏,所以一時未能旅行。現仍注射,當繼續八日或十五日,至邇時始可定行止,故何時行與何處去,目下初未計及也。”
七月二十三日,魯迅日記:“下午須藤醫院之看護婦來注射,計八針畢。”治療又告一段落。同日致雅羅斯拉夫·普實克:“我因為今年生了大病,新近才略好,所以從八月初起,要離開上海,轉地療養兩個月,十月里再回來。”行期由“本月底”推遲到“八月初”了。
……
風月好談 作者簡介
止庵,本名王進文,一九五九年生于北京。隨筆、傳記作家。著有《惜別》、《周作人傳》、《神拳考》、《樗下讀莊》、《老子演義》等,并校訂《周作人譯文全集》、《周作人自編集》、《張愛玲全集》等。
- >
名家帶你讀魯迅:故事新編
- >
我從未如此眷戀人間
- >
苦雨齋序跋文-周作人自編集
- >
月亮與六便士
- >
自卑與超越
- >
推拿
- >
朝聞道
- >
詩經-先民的歌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