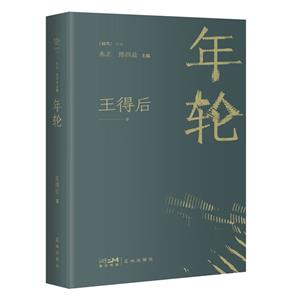-
>
百年孤獨(2025版)
-
>
易中天“品讀中國”系列(珍藏版全四冊)
-
>
心歸何處
-
>
(精裝)羅馬三巨頭
-
>
野菊花
-
>
梁啟超家書
-
>
我的父親母親:民國大家筆下的父母
年輪 本書特色
著名魯迅研究專家王得后隨筆精華結集,喚醒一個時代的文化記憶 1) 著名魯迅研究專家王得后全新隨筆集。 2) 自述早年經歷,回顧魯迅研究往事。 3) 書寫與啟功、李何林、王瑤等老一輩學者的親身交往,反映知識分子的人格與氣質。 4) 特別收錄王得后與日本學者木山英雄的來往信函,呈現不同的學術視角。
年輪 內容簡介
《年輪》是“《隨筆》文叢”之一種,收錄了魯迅研究專家王得后多年以來的重要文章。本書分為三部分,一是作者自述,講述了自己的調入北京魯迅研究室之前的經歷;二是師友記事,記錄了李何林、王瑤、楊霽云、鐘敬文、啟功、李長之、周海嬰等知名學者的言行;三是作者與日本學者木山英雄的來往信札,圍繞周作人相關話題進行深入交流。本書呈現了大量著名學者的治學、為人的真實風采,并記錄了大量知識界的親歷往事,留下了一個時代的文化記憶。“《隨筆》文叢”匯聚《隨筆》雜志創刊以來的核心作者,精選重要文章,呈現文化名人的思想精華,喚醒一個時代的文化記憶。
年輪 目錄
6.目錄
**輯 殘生碎片
寫給故鄉的自述
我一生中的五個偶然
我有三個名字,一個名字有四種寫法
審干審我二十年
我已經死過三次
寫在《魯迅教我》后面
負荊請罪也枉然
紀念魯迅誕生一百周年學術討論會記憶殘片
我點過的燈
寫在《垂死掙扎集》的前面
寫在《垂死掙扎集》后面
第二輯 感念師友
一個人的學問、信仰和作為
——埋在我心中的李何林先生
李何林先生二三事
記李何林先生
王瑤先生
夕陽下的王瑤先生
在霽云師門外
《尋找魯迅》編后記
鐘敬文老師和魯迅先生
為啟功老師祝壽記
啟功老師拜年
啟功老師之墓
詩思詩語中的人性人意之論——紀念啟功老師
李長之老師和魯迅先生
送別周海嬰先生
感念中島碧先生
感懷伊藤虎丸先生
哀悼丸山昇先生
第三輯 書札一束
幾夜滿致魯冀新(2006年11月19日)
敬答幾夜滿道兄(2007年12月8日)
復幾夜滿道兄(2007年12月18日)
關于《北京苦住庵記》的通信(2008年9月6日—2008年11月2日)
致幾夜滿老友(2009年8月23日)
致幾夜滿老友(2015年1月20日)
幾夜滿致魯冀新(2015年1月26日)
致幾夜滿老友(2015年1月28日)
幾夜滿致魯冀新(2019年12月29日)
致幾夜滿老友(2021年1月2日)
幾夜滿致魯冀新(2021年2月22日)
《年輪》編后(趙園)
年輪 節選
夕陽下的王瑤先生 聽說,我沒有親見,王瑤先生中年的時候,還是西裝革履,并且叼著煙斗的。這是真的。大概是一九八八年吧,有一天晚上我們去拜訪先生。臨告別,先生讓蘊如師母拿出一套五張照片送給趙園和我,上面已經題好詞。其中一九六一年的全身像,就是筆挺的西服,烏黑的頭發而且特濃密。那張頭像的輪廓,長長的臉,稍尖的下巴乍一看,像五十年代我們熟悉的一位蘇聯詩人。不過王先生的眼神是嚴厲深邃的。但并不看著你,也不像在沉思挺怪的。先生彌留的時候,不能說話,寫了許多要說的話,三言兩語,斷斷續續的。有一段給大女兒超冰的.說:“我苦于太清醒,分析了許多問題,自以為很深刻,但不必說,不如癡呆好!”我懷疑“不必說”其實是“不能說”。對了,先生那照片上的眼神,就是冷冷的清醒的專注的眼神,卻又向內吸收自己的所見所思的樣子。這些,自然是現在對著照片的遐想。那天晚上雙手接過照片,略一翻檢,心情是別樣的沉靜,而且奇怪:為什么現在送這一套照片呢,題好了詞的? 我認識王先生的時候,他已經“華發滿顛,齒轉黃船”了。那是一九七五年,“*高指示”創建“魯迅研究室”的時期。李何林先生從天津南開大學調到北京,出任魯迅博物館館長兼魯迅研究室主任;又指定從全國幾個省市借調十幾二十個研究人員,而王先生內定為研究室副主任。莫名其妙的是,王先生就在北京,卻遲遲未能報到.我從天津來,反而捷足先登,竟是**個。于是經常盼,經常念叨:王先生怎么還不來呢? 那時我們有政治局批準的八大研究課題,真所謂“極其”繁重而且緊迫呵。 世事就是這樣,隔岸觀火,好像一切都明明白白簡簡單單似的;身在漩渦之中,反而稀里糊涂,手足無措。分明有“紅頭文件”,而且“圈閱”了的,可王先生就是調不來。一方“看來他們是不想‘放’,又不愿說‘不放’因此拖拖拉拉,不解決問題”。一方則只有天曉得。王先生有點尷尬,有點焦急,有點寂寞。他在信里說:“我個人只能‘一切行動聽指揮’。但‘拖’得太久也不好。我希望文物局他們早點與北大商談。估計北大現在是不會斷然不放的。”又說:“我的借調事據北大中文系總支說,已司意借調,但須對北大指導研究生工作有所兼顧,實際上目前并無研究生,何時招考也說不定。我想魯研室方面可以同意。但究竟如何解決,則只有待領導安排而已。”一年多之后,王先生終于被“安排”到了魯研室,算是“借調”。我們這先期“借調”的一批,有的去掉了“借”字,留下來;有的打道回府了。 于是每星期有那么幾天,上午八九點鐘左右,王先生從接他上班的轎車里出來,一手拿著或挾著深褐色的大皮包,叼著或拿著煙斗,一搖一搖上得二樓,走進他的辦公室。下午五點鐘,王先生又一手拿著或挾著深褐色的大皮包,叼著或拿著煙斗,一搖一搖快步走進送他的小轎車綠色上海牌的小轎車,回到北大去。這五點鐘,是準時的。這是李何林先生的脾氣。要不是北大路遠,接王先生的車開出得遲,早上也會八點上班的。王先生有個晚上讀書、看報、寫作到深夜而次日晚起的習慣,臨到該上班的時候,可以想象他的辛苦。 王先生一進辦公室就很少出來。不串門,不談笑,也很少開會。要不開會的時候輪到他不上班,要不開的會只談室里的行政事務,與他無關,他不來。只有中午吃飯的時候,能夠見到王先生,拿著一副碗筷,和我們一道排隊買飯。很快地吃完,涮涮碗,走了。 王先生的辦公室是空里*簡單的。因為我們的大都兼作寢室,內容豐富,也頗有氣氛。王先生的卻名副其實只有一張辦公桌,一把椅子,一對簡易沙發和配套的簡易茶幾,一個書柜里面空空蕩蕩。王先生就在這樣的辦公室坐了兩年:指導我們研究,回答提出的疑難問題,審閱集體編著的《魯迅年譜》。
年輪 作者簡介
王得后,著名學者,作家。1934年生。1957年畢業于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1976年調入北京魯迅研究室,從事專業研究。出版有專著《兩地書研究》《魯迅心解》《導讀》等。
- >
月亮與六便士
- >
煙與鏡
- >
名家帶你讀魯迅:朝花夕拾
- >
姑媽的寶刀
- >
經典常談
- >
史學評論
- >
上帝之肋:男人的真實旅程
- >
月亮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