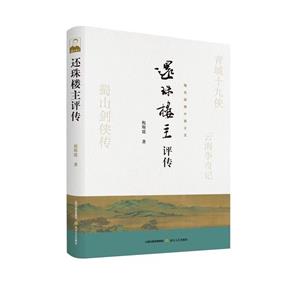-
>
魯迅全傳:苦魂三部曲-增訂版(全三冊)
-
>
大家精要- 克爾凱郭爾
-
>
尼 采
-
>
弗洛姆
-
>
大家精要- 羅素
-
>
大家精要- 錢穆
-
>
白居易:相逢何必曾相識
還珠樓主評傳 版權信息
- ISBN:9787537866934
- 條形碼:9787537866934 ; 978-7-5378-6693-4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還珠樓主評傳 本書特色
還珠樓主是一代傳奇武俠小說作家,是現代通俗小說巨擘,他的生平成就與他的作品一樣耀眼,綜觀其一生,與之相知相交或打過交道的各界名流甚多,在這些不同時期的風云際會中,有些“故事”至今仍是難解之“謎”,但更多的則是傳世之“奇”。
還珠樓主評傳 內容簡介
80多年來,人們都在試圖破譯環繞在還珠樓主身上的這些“謎”與“奇”。本書作者通過近30年的積累,在收集眾多罕見史料和走訪許多當事人的基礎上,經過5年多的寫作、修改,*終完成了這部由引言、10章40節、尾聲組成的43萬字的《還珠樓主評傳》。書中囊括了海內外目前能夠找到的所有相關史料,運用生動的文學語言,完整地再現了傳主波折跌宕的傳奇一生。全書不但史料詳實、內容精彩引人入勝,而且評判精當、客觀公正,是目前海內外首部也是唯一的一部還珠樓主評傳,實為一部填補現代文學作家研究空白之作。 全書配有傳主各時期的相關圖片百余幅。
還珠樓主評傳 目錄
001?? 引言?? 還珠樓主的『謎』與『奇』
019?? **章?? 川東古城,神童降生壯游名山
021 **節 官宦世家誕下“虎崽”
032 第二節 李家祠堂里的“神童”
041 第三節 拜師古怪的王二爺
050 第四節 三上峨眉 四登青城
059?? 第二章?? 少年失怙,姑蘇城里那場戛然而止的初戀
061 **節 客居蘇州 識“珠”生情
070 第二節 眾說紛紜的喪父年月
076 第三節 未來岳父伸出援手
086 第四節 失怙少年眼中的“世態炎涼”
093?? 第三章?? 饑軀北游, 京城仗義行俠的失戀青年
095 **節 沽上省親謀事受阻 京華顧曲入職《晨報》
107 第二節 “應差”內務部的“護花俠客”
118 第三節 孤身遠游 上書吳佩孚“開發西北”
127 第四節 情殤初戀 廁身戎幕
139 第四章?? 踏進津門,涉足梨園再入行伍
141 **節 《大公報》館的雜學編輯
151 第二節 沽上過戲癮 成了尚小云“專職編劇”
161 第三節 結拜段茂瀾 受聘傅作義中文秘書
171 第四節 與朱貞木一同任職電話局
181 第五章?? 師生相戀,轟動平津的『拐帶良家婦女案』
183 **節 緊閉的情窗再次開啟
198 第二節 氣功制服阻撓“師生相戀”的“混混”
208 第三節 打贏了與大中銀行創辦人的“拐帶”官司
226 第四節 《天風報》重金預訂“曠世奇書”
243 第六章?? 操觚鬻文,《蜀山劍俠傳》橫空出世
245 **節 “還珠樓主”筆名寓意與由來
257 第二節 “蜀山”殺青譽滿平津
269 第三節 《蜀山劍俠傳》超凡魔力解密
284 第四節 亙古未有的“大神怪”
299 第七章?? 小報苦耕,推出《還珠樓叢談》與《蠻荒俠隱》
301 **節 披露眾多掌故的《還珠樓叢談》
315 第二節 為劉云若獻出《蠻荒俠隱》
333 第三節 接手“天風” 一人獨編《黑旋風》
351 第四節 病中撰新著 援手“富連成”
363 第八章?? 北平罹難,《青城十九俠》名震南北
365 **節 “青城”爆紅 移居北平
381 第二節 輔佐宋哲元 淪陷中開寫《云海爭奇記》
397 第三節 “十九俠”大鬧紅氍毹 陸小曼來函述仰慕
414 第四節 與張君秋先后身陷日本憲兵隊
431 第九章?? 客居江南,營造紛繁『蜀山系列』
433 **節 只身南下 滬上鬻字獲“買斷”
451 第二節 申城刮起“還珠旋風”
468 第三節 翁婿相認 雙珠重逢
481 第四節 隆隆炮聲中攜眷離滬
493 第十章?? 欣逢盛世,揮筆別舊有新篇
495 **節 姑蘇教子中迎來政權鼎革
511 第二節 履新“天蟾” 痛別“武俠”
529 第三節 北上加盟總政“解放實驗京劇團”
547 第四節 燃情歲月新作連連
567 尾聲?? 『躍進』聲中一病不起
583 參考文獻
591 后記
還珠樓主評傳 節選
1949 年春節過后的二三月間,即將易幟的上海,風行一本名為《還珠樓主論》的小冊子。該書開篇,便是以下文字: 三十七年十二月下旬,上海大公報的地方通信版面,登載著一篇臺灣的通信稿。說有十三個日本人,在臺灣探險,內中十一個人不知所往而終,只活著兩個人還來,寫得非常神秘。 全文如下: 【本報花蓮通信】山地同胞有一個褪色的故事:他們說臺灣屏東與臺東之間有一個大湖,祖先傳說稱為“天上大湖”;面積較之日月潭尤廣,從來無人敢去憑眺。卅三年春天,這個神秘的傳說把日本人誘惑了,當時就有十三個日本人邀著山地同胞領路,準備實踐探險之夢。這條路也是神秘的,一路崇山險峻,人煙斷絕,觸目都是荒涼的原始森林。他們越過一山,山風刮得咄咄逼人,只見古木參天,森林陰暗,一種恐怖的景象,幾乎已非人間。山地同胞指著說:“祖先相傳,由此上去望大湖,從沒有一人回來,我們至此也無法領路了。”日本人聞此并不氣餒,便奮勇自往。他們十一人著黑衣,兩人著白衣。走過幾里,兩人忽然失足鉆入地下,全身不見了。他們大驚,掘開看,原來是堆積著的千年古葉,深已數丈。此時四面圍繞毒蟲的聲音,凄厲如哭泣,森林層層黑暗,人與樹木幾乎都不可辨別。須臾之間,幾個人又鉆墜積葉中了。當晚他們仍未出這驚恐的森林。陰風怒號,一舉火即被熄滅,大家只 得相喚坐到天明。但到天明,幾個人又已失蹤。再過一日,他們力竭之余,不負眾望,果然見一大湖坦然,風光旖旎,獨存天地懷抱之間。但是留下的僅四個人,而且都已迷糊不知歸路,徒喚負負。就憑著各人的命運摸索而返,不幸半路兩人竟又失蹤。直到遠見人煙,方知是誤入屏東境界了。剩下兩人就是當初著白衣的。后來縣政府聞知此事,曾想集團探險,利用湖上的水力發電。但因戰爭正兇,這事也擱置了。據說回來的兩個日本人,并畫了路線,可惜并未為我們所接收,已經帶去日本。 這篇通信,說來頭頭是道,似乎不是完全出于向壁虛構。只要有幾分真實性的話,那真是宇宙之大,無奇不有了。故事雖然很簡短,倒是包括著神怪小說中的各項要素:恐怖、 神秘、陰森、詭異等等。簡直有如一篇雛形的還珠樓主筆下的神怪小說。 現在是科學昌明的時代,可是,以宇宙萬物之浩淼無際而言,人類克服自然的智力,終究還是有限得很。卑之無甚高論,連一個和人類本身*關切的生死之謎,至今仍未打破。誰是不死的?為什么非死不可?為什么不能不死呢?死了誰又知道是怎樣的?為什么不能活轉來呢?于是神怪小說就寄托在這些問號之下而生存了。 宇宙是一個大謎,神怪小說為科學昌明時代的流行小說,是一個小謎而已。〔《還珠樓主論》,徐國楨,上海正氣書局 1949年 2 月出版,第 1—2 頁〕 此段文字中,作者所引《大公報》上有關 1944 年春天日本人恐怖探險的報道,是否真有其事,當時無人核實,現在也很難考證了,但此來自臺灣的“花蓮通信”見諸《大公報》上海版報端,卻是千真萬確的事實。只不過刊出時間不是“三十七年(1948)十二月下旬”,而是 1949 年的“一月五日”,但此“通信稿”文末確有“慧十二月廿日寄”的標注〔《臺湖 上傳奇“天上大湖”——十三個日本人去探險只剩了兩個平安回來》,《大公報·上海版》1949 年 1月 5 日第 5 版〕。在這篇刊于報紙第二張第 5 版、標題為《臺東湖上傳奇“天上大湖”——十三個日本人去探險只剩了兩個平安回來》的“通信”中,集“恐怖、神秘、陰森、詭異”等匪夷所思的內容,足以讓人驚駭,但誠如作者所言:這僅是還珠樓主筆下神怪小說的一個“雛形”。那么,還珠樓主又是何許人也?其神怪小說到底比這匪夷所思的“雛形”還要“恐怖、神秘、陰森、詭異”多少呢? 數十年來,其作為一個神奇之“謎”,始終在撥弄著人們的“好奇”心弦。即使到了今日,敲開“百度”,輸入“蜀山”二字,其相關網頁也是高達近三百萬〔《蜀山劍俠之孽海情天》導讀《情·俠·魔——別具一格的武俠世界》,陳洪,南開大學出版社 2019 年 6 月出版,第 1 頁〕。雖然上文作者認為,在“科學昌明”時代,此“謎”只是“一個小謎而已”,但我們千萬不能忽略其所述的前提——那是與“宇宙”這個“大謎”相較而言。 因此,我們可以說,還珠樓主與其神怪武俠小說自出現之日起,便充滿了匪夷所思的“謎”與“奇”。——八十余年前人們這樣說,今天我們 仍作如是言。 一部《蜀山劍俠傳》連寫十七年出書五十五集達四百五十萬言仍未終結,已令人嘆奇稱謎;其一生共撰武俠小說四十余部總字數高達一千七百萬言,更是奇上加謎、謎上加奇;而其作品中所表現出的劍仙飛俠、神兵利器、佛典道藏、醫卜星相、奇珍異寶、珠宮貝厥、靈禽異獸、山精海魅、瘴氣毒霧、奇峰險境、魑魅魍魎、兇神惡煞等不可羈勒的想象力與描繪力,則更是將這種“奇”與“謎”推到巔峰,令人嘆為觀止,連稱:“奇!奇!奇!”“謎!謎!謎!” 然而,其“奇”與“謎”遠非止此。 曾無槍揮筆身著戎裝四入國共兩黨軍隊的經歷便是一個“謎”,答案 當然是“奇”。 其一生游歷過多少河山,足跡到過哪些地方,也是一“謎”,粗略統計后,又是一“奇”。 《蜀山劍俠傳》寫了五十五集而未終,那么他是否寫完該書,遺稿何方,仍是一“謎”,而答案亦堪稱“奇”。 “拐帶良家婦女案”與“還珠樓主”筆名之由來,未知究竟是個“謎”,知其真相更可稱“奇”。 他讓“蜀山系列”風靡南北、傾倒朝野的“法寶”是個“謎”,而知道了“秘訣”,那簡直就是一部智慧傳“奇”! 綜觀其一生,與之相知相交或打過交道的各界名流甚多,如吳佩孚、傅作義、宋哲元、張自忠、胡景翼、徐樹錚、段茂瀾、周作人、張季鸞、陸小曼、尚小云、周揚、田漢、夏衍、陽翰笙、張君秋、胡金銓、賈植芳、阿甲、馮至、王曉棠,等等。在這些不同時期的風云際會中,有些“故事”至今仍是難解之“謎”,但更多的則是傳世之“奇”。 對其作品臧否軒輊各至極點,則更是這種“奇”與“謎”的具體體現:褒者稱其為“成年人的童話”〔數學家華羅庚語,詳見 1985 年 1 月 3 日《光明日報》〕,七十余年前便有人認為,“中國*著稱的章回長篇神怪小說”不是《西游記》,不是《封神演義》,而是還珠樓主的長篇巨制。“《西游》《封神》尤屬小神怪,《蜀山》《青城》才是大神怪。”〔《還珠樓主論》,徐國楨,上海正氣書局 1949 年 2 月出版,第 14 頁〕當今海外更有學者斷言其作品“乃開中國小說界千古未有之奇觀”。〔《還珠樓主小傳及作品分卷說明》,葉洪生,載《近代中國武俠小說名著大系·還珠樓主卷》,臺灣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1984 年出版,第 4 頁〕 而貶者則斥其小說“荒誕不經”“流毒甚廣”“影響極壞”。就是作者自己也曾在1949 年后,于主流媒體上公開檢討說:“我所寫的這些所謂‘武俠’的荒誕小說,內容都是憑空捏造的,也都是具有反動本質的。”“今天回想過去我寫的那些壞書和它們對讀者的毒害,我真不寒而栗,日夜不安。”〔《一個荒誕、神怪小說制造者的自白》,李壽民(還珠樓主),《北京日報》1955 年12 月25 日,第三版〕 雖然對其作品褒貶不一,但卻有一個特殊現象頗值得人們注意,那就是他寫的“故事”,越是在高知識階層越是受到青睞,有些甚至成了業內后起“大咖”們的范本。六十余年前香港媒體便稱:“還珠樓主的武俠小說打進了知識分子的書齋,那是‘唐人傳奇’以后的僅有現象。比諸同時代的那些武俠小說,他的作品有書卷氣,有想象力,還有浩瀚的人生境界。他的成名作《蜀山劍俠傳》,看似荒誕不經,但他并不是‘為荒誕而荒誕’——媚俗,那里 面其實都是人生的境界。書中隨處皆是佛道思想,但到他筆下,也都是入世的了。”〔《哀還珠樓主》,高翔,(香港)《真報》,1959 年4 月12 日〕而南懷瑾則認為:“現在寫武俠小說的都是亂寫,很多都是偷還珠的東西。”近年更是有學者指出:“在金庸縱橫江湖之前,武俠小說江湖上*亮的金字招牌是什么呢?毫無爭議,《蜀山劍俠傳》!”“‘點珠成金’,……意在指出一個有趣的事實,就是金庸大量(超出一般人想象的)‘偷意’于還珠樓主。”“在金庸的系列小說中,有一個反復出現的情節:外人攪鬧少林寺。……而這些故事的重要源頭恰在《蜀山劍俠傳》之中。”〔詳見陳洪所撰《蜀山劍俠之英瓊傳》導讀《巾幗須眉**人——還珠塑造的**位“女一號”》,第 11 頁;《蜀山劍俠之孽海情天》導讀《情·俠·魔——別具一格的武俠世界》,第 1 頁。兩書均由南開大學出版社 2019 年 6 月出版〕 此外,21 世紀之初,由《亞洲周刊》與來自全球各地的文學名家聯合評選的“二十世紀中文小說一百強”揭曉,赫然在列者,除魯迅的《吶喊》、沈從文的《邊城》、老舍的《駱駝祥子》、張愛玲的《傳奇》、錢鍾書的《圍城》、茅盾的《子夜》、白先勇的《臺北人》、巴金的《家》、蕭紅的《呼蘭河傳》等新文學作品外,還有還珠樓主的《蜀山劍俠傳》。對此,誠如論者近年所言:“還珠樓主的作品上榜,并非評委們制造噱頭,而是反映出了評選標準更趨全面,更趨合理。若從社會影響力、文化傳承,以及獨創性來看,還珠上榜實在是實至名歸。”〔《云海爭奇之兒女恩仇記》導讀《恩仇肝膽——還珠系列中*耀眼的明珠》,陳洪,南開大學出版社 2019 年 6 月出版,第 1 頁〕 褒貶反差如此之大,這不能不說是一個耐人尋味的問題。其實問題本身就是一個“謎”,而且這個“謎”的答案,絕對可稱拍案驚“奇”! 也正因此,近一個世紀以來,人們都在試圖破譯環繞在還珠樓主身上的這些“謎”與“奇”。 然而世事無常亦詭異。大紅大紫于民間的還珠樓主,誠然讓各色人等既“猜謎”又“嘆奇”,但由于托舉其“謎”與“奇”的一千七百萬言神怪武俠作品,無論是在 1949 年以前或以后,均處于游離“普世價值”之外且“難登大雅”的文學“妾身”地位,故而造成“小報小刊”及民間市井喝彩者眾、“主流媒體”與研究機構評騭者寡的局面。這種局面釀成的 結果,那便是人們在對還珠樓主既“猜謎”又“嘆奇”的同時,也試圖揭開籠罩在其身世之上的神秘之紗。 其實,自還珠樓主神怪武俠小說面世之日起,對其人其書的褒貶與爭 論便已開始。 民國以降,與其作品暢銷相伴而生的“褒貶”雖已頻現南北“小報小刊”,然而目前除了個別篇目被發現并為研究者所反復引用外〔如牛史的《還珠樓主受警告,能否在上海保持小說家地位》(《風光》1946 年 3 月 24 日);羽生的《還珠樓主像袁世凱?》(《大地》1946 年 6 月 21 日);《還珠樓主的怪事》(香港《大公報》1956 年 3 月 1 日);高翔的《哀還珠樓主》(香港《真報》,1959 年 4 月 12 日)等,都是對還珠樓主及其作品的評騭〕,其余則大多湮沒于塵封的故紙堆中,有的沉睡經年尚待開發,更多的則隨著歷史煙云而灰飛煙滅。現今能看到且被研究者共同認為民國時期較全面評介還珠樓主其人其書的專著,便是本“引言”開篇所摘引的那本小冊子——1949 年 2 月上海正氣書局出版的徐國楨所著《還珠樓主論》〔《還珠樓主論》乃徐國楨根據他 1948 年在上海《宇宙》雜志復刊號第 3、4、5 期上連載的《還珠樓主及其作品之研究》一文增刪整理而成〕。雖然該書極薄,僅有區區五十二頁三萬余字,但足以稱其為民國時期對還珠樓主與其代表作《蜀山劍俠傳》進行研究的“權威著作”,至今仍被海內外操此業者頻繁垂青并廣為 引用。 《還珠樓主論》出版之際,正值國共對決的關鍵時刻。八個月后,國民黨政府退守臺灣,新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此后一年,海峽兩岸罕見地實施了同一文藝政策:武俠小說遭到全面禁毀。 自此之后,在中國,無論是大陸還是臺灣地區,武俠小說的創作與出版均進入了冰凍期。 大陸武俠小說遭禁,后文將有詳述;臺灣地區武俠小說被禁,內幕則鮮為人知。據相關研究者近年披露,1949 年以后,臺灣地區滿天飛的文藝口號是“戰斗的時代”,帶給文藝以戰斗的任務。以政治意識為主導的軍中文學,占據了主導地位。文學創作與整個社會一樣,處于僵硬板結的狀態。純粹的類型化的武俠小說受到打壓。尤其是 1959 年 12 月 31 日, 由“警總”負責規劃執行,專門針對坊間流傳的通俗文學展開了一次掃蕩行動。1960 年 2 月 15 日至 17 日,在全省各地同步取締所謂的“共匪武俠小說”,這次行動被稱為“暴雨專案”。據 1960 年 2 月 18 日《中華日報》第三版記載,“警總”于數天之內,就取締了九十七種十二萬余冊之多,許多武俠小說出租店,幾乎“架上無存書”;而《查禁圖書目錄》所列“暴雨項目查禁書目”則高達四百多種,其中九成以上是大陸“舊派”及香港地區金庸、梁羽生的作品。〔《中國臺、港、澳地區通俗小說的創作語境和價值評估》,湯哲聲,《中國當代文學研究》2021 年第 2 期。參見《臺灣武俠小說發展史》,葉洪生、林保淳,臺灣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005 年出版,第 133 頁〕在大陸“舊派”書目中,還珠樓主的《大俠狄龍子》《青城十九俠》《蜀山劍俠傳》(誤寫為《獨山劍俠》)赫然在列〔《臺灣查禁武俠小說之“暴雨專案”始末探析》,林保淳,《西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 年第 2 期,第 27 頁〕。 香港地區是個例外。在大陸與臺灣地區武俠小說噤聲期間,港島一地卻獨延一脈。不但 20 世紀 50 年代中期報紙連載熱鬧非凡,創作出版熱火朝天,各名家紛紛崛起,競相于“紙上江湖”擺擂開賽,直殺得硝煙四起、天昏地暗,而且在對武俠小說和還珠樓主研究方面,也是勇于發聲,見地非凡。1959 年 12 月,胡適在香港媒體發出“武俠小說是下流的”聲音。旋即,身在港地的倪匡便公開撰文表示反對。幾乎與此同時,金庸創刊了文史刊物《武俠與歷史》。在創刊號上,他發表了燕人所寫《還珠樓主的武俠小說》一文,其中針鋒相對地指出: 一種小說能為廣大群眾所接受,必有其原因。多少年來,新式的衛道君子們,大聲疾呼,反對神怪武俠小說,視如洪水猛獸,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而神怪武俠小說的作者面臨社會對他們的譴責,似乎極少反抗。本來神怪武俠小說在這一情勢之下,早該銷聲匿跡,無立足之余地了。為什么時至今日,神怪武俠小說不但未見絕跡,而且反而囂張愈甚呢?這其間,自有配合于社會心理方面的必然的原因。換句話說,就是先有這么一個畸形的社會,然后才有那些畸形的小說的。 對于還珠樓主,作者更是盛贊曰: 在近代中國許多武俠小說的作者之中,以“還珠樓主”作為筆名的李壽民先生,一直是享譽*盛的一個。他的作品不但在若干年前的國內影響力極大,就是在今天的海外,仍然不斷地流傳著,使許多讀者愛不忍釋。 還珠樓主的作品究竟為什么能這樣得到人們的普遍歡迎呢?在海外我曾經將這個問題請教過他的一位忠實讀者,他的答復是這樣的: 還珠樓主的小說,不論在文筆上、在結構上、在思想上,都是具有強烈的中國風味。他雖然采用了聲光電磁等原理,仍是極其淺近,是把科學硬拉到玄學之內,不是正面的接受科學。不能算是受到了歐西學說的多大影響,無損乎外形內質之同為“中國式”。 尤其是在文筆方面,像他這樣富于保守性,在今日的小說作家中已不多了,歐化的句法,他那里決不會發現半句,就是新的名詞,也少得幾乎沒有。不是純粹的文言,也不是純粹的 白話,文言白話,常是互相夾雜著,字句很短練,修辭很簡單〔《還珠樓主的武俠小說》,燕人,(香港)《武俠與歷史》第 1 期,1960 年 1 月 11 日出版,第 26、28 頁〕。 此文對還珠樓主“講好中國故事”和其作品的“中國氣派”,做了高度贊許。 香港地區的這種“熱鬧”,也在刺激著海峽兩岸。 雖然大陸于 1951 年在新文學家鄭振鐸的倡導和時任中央文化部部長、新文學家沈雁冰的批準下,自當年 6 月起全面禁止武俠小說,由此造成了此后 30 年武俠小說創作與出版空白期。但在民間,武俠小說卻是不脛而走,仍在悄然流行。 相較大陸,臺灣地區稍顯松動,有禁難止。尤其是還珠樓主的《蜀山劍俠傳》,不但讓成年人難以忘懷,而且由于其光怪陸離的“童話”魅力,反而又重新吸引了一批新的少“蜀山迷”。據臺灣武俠小說研究專家葉洪生回憶:“首次聽到‘還珠樓主’之名,是來自于先母,一位不折不扣的‘老蜀山迷’。不過她老人家生前閑話家常時,總是這樣說:‘不知道 是為啥,當時我們大家都習慣叫還珠樓;大概是真有一座寫字樓也說不定,否則怎么有樓主呢?這個還珠樓主呀,可了不得 ! 天上地下無所不知。他寫的《蜀山劍俠傳》更是想入非非,無奇不有!敢說遠遠超過《西游記》《封神榜》,真好看極了 !’”〔《還珠樓主散文集》序一,葉洪生,(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2014 年 10 月出版,第 3 頁〕 正是在母親的影響下,生活在臺灣地區的葉洪生,很小便與還珠樓主 及其《蜀山劍俠傳》結緣: 回首前塵,與《蜀山》結下不解之緣,遠在 1956 年我正念小學三年級的時候。說來有趣,初見《蜀山》并非在書肆中,而是在孩童們常用來玩耍的圓形紙牌上。那時,“打圓牌”的游戲極為風行,小學生課余均趨之若鶩!我由圓牌上所印的圖案而認識《蜀山》人物;繼而由“小人書”(連環圖畫)上,進一步得悉《蜀山》故事——及至看到神駝乙休被困銅椰島、倒翻地肺這一折,不禁眉飛色舞,神為之奪!然而好景不常,《蜀山劍俠連環圖》流行一陣,忽焉絕跡市面。在這當口上,欲罷不能的“小蜀山迷”只好入書肆、尋仙蹤,租來一本本《蜀山》原著,埋頭苦讀那密密麻麻、內蘊玄機的“有字天書”!記得那時年紀太小,識字不多,囫圇吞棗看《蜀山》,只能看熱鬧而不能看門道;于其中的精微奧妙之處,全然無法領會。及年事稍長,重溫《蜀山》,方漸如倒啃甘蔗,真味盡知。〔《蜀山劍俠評傳》代序,葉洪生,(臺灣)遠景出版公司 1982 年 10 月出版,第 9—10 頁〕 由此可見,在 1950 年以后的臺灣地區,武俠小說創作與出版雖然遭禁,但在民間的少兒游戲中,還珠樓主的作品還是變相出現,而且在市井的租書鋪中,還珠樓主等武俠名家的小說仍在暗中流傳,并由此影響和造就了新一代武俠“粉絲”與“蜀山迷”。 正是在此環境之下,對武俠小說尤其是還珠樓主《蜀山劍俠傳》情有獨鐘的葉洪生,開始廣為收羅海內外市井民間的還珠樓主作品,“磨劍”二十余載,*終于 1982 年 5 月在臺北《民生報》副刊連載《驚神泣鬼——話〈蜀山〉》長文,繼 1949 年徐國楨《還珠樓主論》之后,再次向世人彰顯了還珠樓主傳奇與《蜀山劍俠傳》魅力。隨后,在此文基礎上, 他再賈余勇,經增補改寫,完成《蜀山劍俠評傳》一書,并于當年 10 月由臺灣遠景出版公司付梓。對此,他曾言:“為了打破臺灣當局無聊的政治禁忌,我刻意在《蜀山劍俠傳》的書名中加上一個‘評’字,以達到彰顯《蜀山》之目的。”〔《天下**奇書〈蜀山劍俠傳〉探秘》新序,葉洪生,學林出版社2002 年 2 月出版,第 13 頁〕此書之后,葉洪生“再接再厲,又借主編、批校、評點《近代中國武俠小說名著大系》的機緣,排除萬難,平反《蜀山》,重新出版葉批本,終于使這部絕代武俠奇書在冰封入土三十年后,能夠霍然解凍,重見天日!時維 1984 年冬,距拙著《蜀山劍俠評傳》之拋磚引玉,僅只兩年光景,不可不謂是奇跡”。〔《天下**奇書〈蜀山劍俠傳〉探秘》新序,葉洪生,學林出版社 2002 年 2 月出版,第 13—14 頁〕 這一系列行動帶來的后果,便是促使臺灣當局對武俠小說的全面解禁。十七年后,回首前塵,對當年情景,葉洪生仍感慨系之:“俗話說:‘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單憑區區一股傻勁,仗義為中國通俗文學寶貴遺產——即所謂‘舊派’武俠小說請命,竟一舉突破臺灣當局‘暴雨專案’禁令,促使‘舊派’武俠名著全面解放,實乃個人一生*大的榮幸!”〔《天下**奇書〈蜀山劍俠傳〉探秘》新序,葉洪生,學林出版社 2002 年 2 月出版,第 14 頁〕 據此可知,武俠小說在臺灣地區打破“暴雨專案”,全面解禁,葉洪生先生厥功至偉。而他所執打開“舊派”武俠“禁庫”的鑰匙,就是還珠樓主的《蜀山劍俠傳》。 與葉洪生“平反”武俠小說同時,還珠樓主舊友、掌故大家唐魯孫與還珠樓主長子李觀承,也分別于 1982 年在臺灣地區媒體上發表了《我所認識的還珠樓主——兼談〈蜀山〉奇書》《關于我的父親還珠樓主》兩文;隨后,定居美國西雅圖的還珠樓主研究專家黃漢立,又于 1984 年發表《論〈蜀山〉后傳之真偽》一文。由于他們與葉洪生的相互呼應,一時間,“還珠熱”升溫。 臺灣地區武俠小說的解禁,也讓大陸文學界和出版業看到了還珠樓主“真面”。尤其是葉批本《近代中國武俠小說名著大系》(內收還珠樓主小說 6 部,分別為《蜀山劍俠傳》《峨眉七矮》《青城十九俠》《柳湖俠隱》《北海屠龍記》《蜀山劍俠新傳》),于 1984 年 12 月由臺灣聯經出版事業公司推出后,隨著兩岸各種文化交流的展開,“還珠樓主”遂不脛而走,通過各種渠道進入大陸。盡管這一時期仍是作為“地下讀物”,僅在民間傳閱,但畢竟聊勝于無,讓大陸文學與出版業由此看到了“主流”作品之外的另一道奇幻風景。 轉機出現在 20 世紀 80 年代中期。隨著改革開放政策的深入,金庸、梁羽生、古龍等港臺“新派”武俠小說“繁體本”在大陸民間開始悄然流行。嚴家炎、馮其庸、章培恒、范伯群、徐斯年、寧宗一、張贛生、潘蕪等著名學者,敏銳地洞悉了“新派”武俠小說的文學成就,同時也引起他們對當年閱讀“舊派”武俠小說的回憶,并進而發現了兩者間的承繼關系。尤其是 1987 年 12 月,香港中文大學主辦了“國際中國武俠小說研討會”,標志著武俠小說研究正式進入學術殿堂。此次大會邀請了余英時、劉紹銘、葉洪生、許倬云等諸多著名學者參會。翌年 3 月 12 日,在北京出版的《文藝報》以《武俠小說初登學術殿堂》為題,報道了此次大會。同年,北京等地的《讀書》《文藝爭鳴》《學林》等學術刊物開始發表評介武俠小說的文章。 學界的發聲傳遞了禁錮松動的信號。自 1951 年 6 月大陸全面取締武俠小說創作與出版之后,此時國家沒有任何“文件”下發,一些出版社便在不失時機地推出“新派”武俠小說的同時,也“捎帶”整理、出版了民國“舊派”武俠小說。而在初期,這些“搭車”出版的“舊武俠”中,十之八九則是直接“盜用”了葉批“大系”。
還珠樓主評傳 作者簡介
倪斯霆,1961年出生,天津人,編審。曾供職天津市出版研究室。中國武俠文學學會理事、中國俗文學學會會員、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會員、天津市解放區文學研究會理事、天津市新聞工作者協會理事、天津市紅樓夢學會理事、天津市作家協會會員。從事民國通俗小說及天津近現代文學史、出版史、新聞史研究三十余年。在《新文學史料》《文史知識》《通俗文學評論》《民國春秋》《縱橫》《新聞出版博物館》《天津文史》等十余家文史刊物、數家大學學報及國際國內學術會議論文集中發表論文四十余篇,在《中華讀書報》《藏書報》《天津日報》《今晚報》《中老年時報》等報紙發表文章數百篇。文章多次被《新華文摘》《人民日報》《光明日報》《文匯報》《文摘報》《作家文摘》及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料中心轉摘。出版專著《舊人舊事舊小說》《舊文舊史舊版本》《舊報舊刊舊連載》《還珠樓主前傳》《文壇書苑憶往錄》《老天津的文壇往事》等。
- >
唐代進士錄
- >
名家帶你讀魯迅:朝花夕拾
- >
伊索寓言-世界文學名著典藏-全譯本
- >
詩經-先民的歌唱
- >
中國人在烏蘇里邊疆區:歷史與人類學概述
- >
苦雨齋序跋文-周作人自編集
- >
隨園食單
- >
大紅狗在馬戲團-大紅狗克里弗-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