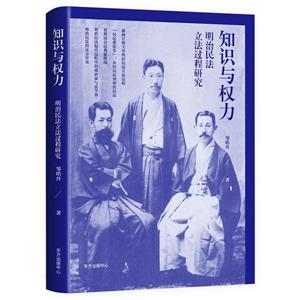-
>
法律的悖論(簽章版)
-
>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
>
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
-
>
私人財富保護、傳承與工具
-
>
再審洞穴奇案
-
>
法醫追兇:破譯犯罪現場的156個冷知識
-
>
法醫追兇:偵破罪案的214個冷知識
知識與權力:明治民法立法過程研究 版權信息
- ISBN:9787547320006
- 條形碼:9787547320006 ; 978-7-5473-2000-6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知識與權力:明治民法立法過程研究 本書特色
適讀人群 :一般讀者1. 明治維新后的日本如何改正與西方列強簽訂的不平等條約,廢除領事裁判權、收回關稅自主權,實現國家獨立乃至“與萬國并立”?在體制變革的過程中,如何維持政治秩序穩定,并為經濟社會發展提供法律保障?本書聚焦明治日本對這一時代課題的法律回應。 2. 從政治史的角度探討明治民法立法得以成立的原因、背景及具體立法過程,再現近代日本立法者們面對外部壓力和內部變革,圍繞民法典編纂的決策、起草和審議,在政治和社會層面展開的激烈的知識與權力博弈。這是認識日本國家和日本人的一個重要方面。 3. 包括民法典在內的近代日本法律制度、法學體系建設,是對西洋法律及法學的創造性轉化,并深刻影響了東亞鄰國的法律現代化進程。本書有助于人們在東西方文明交流與影響的視角下,思考近代以來東亞社會對西方法制及法學的移植、模仿、吸納和創新。
知識與權力:明治民法立法過程研究 內容簡介
本書以明治民法典的繼受法身份作為研究基準,在政治史大背景下,從知識與權力的互動關系出發,具體探討明治立法者們(官僚、政治家與法學者)對明治民法立法過程產生的影響。作者認為,明治民法典的立法過程是知識與政治綜合作用的結果。即藩閥權力主導下的舊民法立法過程既體現了在西洋法知識的繼受過程中權力的偏向作用,也體現了權力在知識影響下對立法方針的調整與采擇;受到條約改正的影響,民法典從受到些微關注一躍成為輿論焦點。學者及輿論對此加以回應,圍繞舊民法命運而產生的民法典論爭不僅是學理論爭,同時也是政治斗爭,更是主動將知識輸入政治決策過程的斗爭;舊民法的政治審議過程既是民法典論爭的延續、學者將法律知識輸入政治決策過程而導致的客觀結果,也體現了政治大環境下圍繞舊民法審議而暴露的種種權力斗爭;明治民法的起草過程是針對舊民法修正而形成的知識立法成果,體現了官僚、政治家在起草過程中對立法大原則的掌控,同時也體現了法學者延續知識和維護其獨立性的立法貢獻;明治民法的審議過程不僅體現了知識在審議過程中受到權力影響而體現的弱勢,也體現了權力在審議過程中因知識的匱乏而產生的無力感。
知識與權力:明治民法立法過程研究 目錄
序言
序章
一、問題緣起
二、研究綜述
三、研究方法
**章 藩閥官僚主導的舊民法立法過程
**節 萬國公法引入與江藤新平“兵法一致”觀下的民法立法
第二節 西洋國內法引入與大木喬任“國體民情”觀下的民法立法
第三節 法德洋學競爭與山田顯義的“內外兼顧”觀下的民法立法
第二章 “民法典論爭”:從舊民法到明治民法
**節 “民法典論爭”前的民法立法論
第二節 “民法典論爭”
第三節 輿論導向的民法典反對論
第三章 初期議會法典延期戰
**節 **次帝國議會商法典延期戰
第二節 第三次帝國議會民法商法延期戰
第三節 伊藤博文與舊民法的廢棄
第四章 明治民法起草過程中的政治家與法學界
**節 伊藤博文與法典調查會
第二節 法典調查會的運作及民法起草
第五章 明治民法的議會審議
**節 第九次帝國議會財產法部分審議
第二節 第十二次帝國議會家族法部分審議
第三節 明治民法頒布、改正條約實施與“七博士事件”
終章
一、明治民法典立法的知識性
二、明治民法典立法的權力性
三、明治民法立法——知識性與權力性的互動
參考文獻
知識與權力:明治民法立法過程研究 節選
終章 明治維新到明治憲法體制的確立是條約改正的時代,同樣也是政治性革命與文化性革命的時代。明治民法典立法過程體現了明治民法作為繼受法而造成的理論困境,雖然繼受法立法的核心問題是如何令西洋母法適應本國的國情,但是無論是政治家、官僚,還是學者、思想家都無法回答這個問題。這是明治維新所造成的知識斷裂與西洋制度引入而引起的社會變化共同作用的結果,以此時代為背景而形成的明治民法典立法過程是知識與權力共同作用的結果。 一、明治民法典立法的知識性 舊民法立法所體現的知識性是潛藏在社會思潮背后的,此時接受西方繼受法知識時日尚短,民法學在學界不具備獨立的發言權,僅能跟隨著思想界的呼聲隨波逐流。它首先受到跟隨萬國公法繼受而引入的自然法、性法觀的影響,其后受到憲法思潮、法制官僚對于西方國家構想反思的影響,表現出對于慣習的重視;隨著明治十四年政變的發生,傳統儒學和德國學的地位因克制英法自由主義而加強,產生了德國派、英國派、法國派三足鼎立的繼受法局面,其中還摻雜著傳統儒學的因子。本國法學不強大的現實,亦迫使政治家選擇外國法學者作為法典草案的起草者,也引起了德國法學派與法國法學派在政權內部依靠法理而進行的政治較量。 “民法典論爭”雖然無法回答繼受法立法的核心問題,但是它向政府發出信號,主動要求本國法學家在民法立法中的決定性地位,它隨著非條約改正的浪潮在社會輿論中日漸勢大。同時,它主動與政權相結合,無論是延期派還是斷行派,皆是此次論爭的受益者,因為正是靠著內部論爭所引發的爭端,本國法學者向政權證明了自身的獨立性,令他們有資格參與民法修正,給予他們機會展示自身的法學素養。 正如穗積陳重所言:“法典編纂固為政府之行為,但是如若無法得到全體法律家之翼贊,則不能輕易奏其功效。蓋一國法律思想落后,國民中如果沒有產生一種所謂的法律家族群,就可以認為沒有必要得到法律家的輔助編纂法典,但是振興法律學,增加學者、裁判官、代言人,使法律從業者產生于民間,對其立法、司法大業儼然擁有話語權,如此法典編纂、法典頒布之后,才可以實地任用裁判官、代言人以及學者從事法律注解批評工作,其不可之時,其編纂難成,自不待言。” (穂積陳重:《法窓夜話》,第 179頁) 雖然研究證實舊民法與明治民法在內容上沒有什么不同,但是明治民法是本國法學家獨立立法的產物,是本國法學者面對繼受法知識和本國傳統慣習的矛盾獨立作業的成果。他們以近代法理為指導思想,以社會環境為評判標準,寬容當時依然存在的過時舊慣,將立法的視野擴展至將來,利用立法技術限制舊慣對社會生活的破壞作用,獨立思考,獨立判斷,體現了知識自身發展的獨立性。 與此同時,民法典的制定對于社會關系的整合及其體系化具有重大意義。民事單行法規只能處理本領域的具體問題,各個單行立法間卻無法進行邏輯化、體系化的融會貫通,從而導致立法狀態碎片化。反之,法典并非以前各種情況下個別的、斷裂的諸法令的匯集,它對于各種應急的、廢止的、變更的法令皆具有限定意義,連接全部的、零散的、個別的單行民事法規,具有因將來時代的變化而進行部分改正的可能性,乃總體上國家永恒的法規。因此民法典之于日本,除了條約改正的必要性之外,更具有一種象征性的意義,象征著文明、進步的維度。 二、明治民法典立法的權力性 從明治初年江藤新平確定民法立法開始,到明治民法立法結束,無論是舊民法還是明治民法,其根本目的皆是著眼于內政,有利于外交的。江藤新平的“兵法一致”觀著眼于內部整頓,他的政治理想是通過民法立法規范日本國民的日常生活,以此迎接西洋的沖擊。他受到萬國公法的啟發,在性法理念支配下認為一切法律皆有移植的可能性,奮不顧身投入本國民法立法的事業當中,沒有經過深思熟慮,確實有些冒進的嫌疑,其中也存在著明治初年繼受法貧乏的客觀狀況,但是其冒進的本質屬性卻并非以改正不平等條約為目的。 大木喬任擔任民法編纂局總裁長達六年,社會思潮中對于憲法、刑法、民法的反思以法制官僚井上毅等為載體延伸入政府內部,引發了繼承法論爭。多年的司法卿裁判經驗令大木在采用繼受法形式立法時更為重視社會慣習層面,令他采取任用外國人起草財產法、本國人起草家族法的雙軌制立法模式,此舉開辟了社會慣習調查的先河。在條約改正的態度上,大木的態度極為端正,重視主權勝于一切。 山田顯義被稱為法典伯,在他任法典取調委員會總裁期間制成了舊民法和舊商法。他受命于危難之際,盡力采取內外兼顧的態度,一方面撥亂反正,調整井上馨法律取調委員會時期差點喪失立法權獨立性的狀態,在立法戰略上采取謹慎態度,另一方面在戰術上,他以強權加強立法力度,為條約改正鋪平道路。此等左右逢源的態度招致元老院的不滿,山田自身的固執也未令矛盾得到調和,舊民法自此擁有了體制內的*大敵人,以村田保為代表的元老院勢力站到了舊民法的對立面。 時值《大日本帝國憲法》頒布,國內民眾摩拳擦掌,躍躍欲試,妄圖臧否任何事件,在人潮中找到自己的聲音;而非條約改正運動也沸沸揚揚,國內彌漫著一種民族主義性質的懷疑主義氛圍。舊民法竟然在這樣一個敏感的時間點頒布,還因為其尷尬的繼受法身份招致法學者的不同評論,無疑雪上加霜。它失去了得到社會寬容和理解的機會,更何況當時的社會根本對任何事情都不打算采取寬容和理解的態度。第三次帝國議會時期,議會通過民法、商法延期案,山田顯義身死,大木喬任離職,意味著舊民法失去了*后的政治庇護,它的生命也自此走到了盡頭。 明治民法則因第二次伊藤博文內閣的建立而獲得了良好的生存空間。伊藤博文對于舊民法的態度曖昧,是主動的斷行派,被動的延期派。他以條約改正作為奮斗目標,民法立法則是其實現條約改正的必要條件。但是條約改正的重大挫折令以往對于民法典立法持旁觀態度的伊藤博文轉而重視明治民法的立法工作。他希望建立行政權高于立法權的“行政國家”,而模仿法國民法的舊民法中存在許多限制行政權的規定,有礙“行政國家”的建立,*終被拋棄。伊藤博文轉而決定模仿德國式民法制定新民法。他采取學政分立、權責明確的態度經營法典調查會,在把握進度和人事以及民法立法大方向的同時給予了本國法學者足夠的起草自主性。 在明治民法的審議過程中,面對改正條約實施在即的壓力,伊藤博文甚至不惜利用略帶威脅的口吻對議會加以勸說誘導,其自身的實力對議會來說本身就是一種威壓,議會在此情況下不得不采取順從政府的態度盡速審議,明治民法終于在伊藤博文的保駕護航下有驚無險地獲得了合法性。 三、明治民法立法——知識性與權力性的互動 立法是一種主權國家的行為,是社會實踐抽象化為國家制度的過程,民法典立法更是因為其本身的知識屬性和作為政治立法而產生的權力屬性而需要經受更多的考驗。 首先,民法典立法過程中必須經過三道門檻,**道起草,第二道審議,第三道才是社會實踐。前兩道試題皆屬于國家權力主導下的考試,所以說,民法典立法首先需要通過國家權力的檢驗,然后才可以付諸社會的考驗。 其次,無論起草階段還是審議階段,皆充斥著知識性立法與權力性立法兩大原則,前者確立立法方針,決定立法內容;后者明確立法方向,給予立法環境,影響立法進度,民法典立法乃是由法學家與政治家共同完成的。 再次,政治家從政治需求角度確立立法方向,對于立法知識加以選擇,此種選擇同樣受到知識和政治兩方面的影響,前者分為知識對政治的主動性影響和被動性影響,后者代表了局部政治必要性和整體國家大環境。 政治家容易察覺知識對自身的主動性影響,但是也因唾手可得而不容易判斷其利害得失,令其取舍兩難;他們不容易察覺知識對政治的被動性影響,但此種影響又是潤物細無聲的,是不可抗拒的,容易為政治家的潛意識所吸收,而于某次機會中脫穎而出,對其政治判斷產生很大影響。江藤新平、大木喬任、山田顯義、伊藤博文,這些政治家在確定民法的立法方向時,受到知識界對民法立法看法的影響,同時也以自身的知識儲備為判斷依據,決定日本到底是應該編纂法國式的民法,還是德國式的民法。
知識與權力:明治民法立法過程研究 作者簡介
鄒皓丹,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北京大學歷史系世界史專業博士,上海交通大學東京審判研究中心博士后。長期從事東亞近現代法律史、政治文化等領域的研究。在《史林》《華東政法大學學報》《暨南學報》等刊物上發表論文多篇。
- >
伊索寓言-世界文學名著典藏-全譯本
- >
我與地壇
- >
名家帶你讀魯迅:故事新編
- >
煙與鏡
- >
伯納黛特,你要去哪(2021新版)
- >
小考拉的故事-套裝共3冊
- >
【精裝繪本】畫給孩子的中國神話
- >
山海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