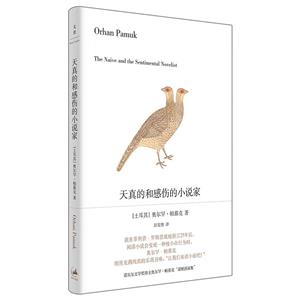-
>
百年孤獨(dú)(2025版)
-
>
易中天“品讀中國(guó)”系列(珍藏版全四冊(cè))
-
>
心歸何處
-
>
(精裝)羅馬三巨頭
-
>
野菊花
-
>
梁?jiǎn)⒊視?/p>
-
>
我的父親母親:民國(guó)大家筆下的父母
天真的和感傷的小說家 版權(quán)信息
- ISBN:9787208107410
- 條形碼:9787208107410 ; 978-7-208-10741-0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cè)數(shù):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天真的和感傷的小說家 本書特色
適讀人群 :廣大讀者2006年諾貝爾文學(xué)獎(jiǎng)得主 奧爾罕·帕慕克作品 截至本書,帕慕克的重要作品已全部出齊。 2009年帕慕克應(yīng)邀在哈佛大學(xué)做了六場(chǎng)演說,即著名的諾頓演說,此為結(jié)集。大家熟悉的博爾赫斯的《詩藝》,卡爾維諾的《新千年文學(xué)備忘錄》,也一樣出自這里。 一個(gè)小說家對(duì)讀者的揭秘與渴望。 成就奧爾罕·帕慕克的文學(xué)省思。 更是中國(guó)讀者熟悉的老帕,充滿純真的樂觀召喚大家——“讓我們來讀小說吧!” 對(duì)于現(xiàn)代的世俗化個(gè)人來說,要在世界里理解一種更深刻、更淵博的意義,方法之一就是閱讀偉大的文學(xué)小說。我們?cè)陂喿x它們時(shí)將理解,世界以及我們的心靈擁有不止一個(gè)中心。 ——奧爾罕·帕慕克
天真的和感傷的小說家 內(nèi)容簡(jiǎn)介
收錄帕慕克2009年在哈佛的諾頓演講,總共六篇。同時(shí)附有老帕的后記,講述這些文字的起因,及在美國(guó)的一些生活與創(chuàng)作等。
天真的和感傷的小說家 目錄
1 閱讀小說時(shí)我們的意識(shí)在做什么
2 帕慕克先生,這一切真的都在你身上發(fā)生過嗎?
3 文學(xué)人物,情節(jié),時(shí)間
4 詞語,圖畫,物品
5 博物館和小說
6 中心
收?qǐng)霭住?
天真的和感傷的小說家 節(jié)選
1 閱讀小說時(shí)我們的意識(shí)在做什么 小說是第二生活。就像法國(guó)詩人熱拉爾 ·德 ·奈瓦爾( Gérard deNerval)所說的各種夢(mèng),小說顯示了我們生活的多樣色彩和復(fù)雜性,其中充滿了似曾相識(shí)的人、面孔和物品。我們?cè)陂喿x小說的時(shí)候,恍若進(jìn)入夢(mèng)境,會(huì)遇到一些匪夷所思的事物,讓我們受到強(qiáng)烈的沖擊,忘了身處何地,并且想像我們自己置身于那些我們正在旁觀的、虛構(gòu)的事件和人物之中。當(dāng)此之際,我們會(huì)覺得我們遇到的并樂此不疲的虛構(gòu)世界比現(xiàn)實(shí)世界還要真實(shí)。這種以幻作真的體驗(yàn)一般意味著我們混淆了虛構(gòu)世界和現(xiàn)實(shí)生活之間的區(qū)別。不過,我們從來不抱怨這種幻象,這種天真的做法。相反地,我們情愿我們所閱讀的小說可以和一些夢(mèng)一樣延綿不斷,真心希望這種第二生活可以持續(xù)地激發(fā)我們一種現(xiàn)實(shí)感和真切感。盡管我們知道小說是虛構(gòu)的,可是如果一部小說不能延續(xù)真實(shí)生活的幻象,我們就會(huì)感到不安和煩躁。 做夢(mèng)的時(shí)候,我們以為夢(mèng)境是真實(shí)的。這就是夢(mèng)的定義。閱讀小說時(shí),我們同樣以為小說是真實(shí)的——但是我們心里也明白這種想法純屬虛妄。這種悖論源自小說的屬性。我們?cè)诖藦?qiáng)調(diào)指出,小說藝術(shù)依賴于我們可以同時(shí)相信兩種矛盾狀態(tài)的能力。 四十年來,我一直在閱讀小說。我知道,我們可以對(duì)小說采取多種姿態(tài),我們可以采用多種方式把我們的靈魂與意識(shí)投入到小說之中,既可以輕松地,也可以嚴(yán)肅地對(duì)待小說。正是這樣,我已親自體驗(yàn)獲知閱讀小說的多種方式。閱讀小說,我們有時(shí)候以合乎邏輯的方式,有時(shí)候只以目視,有時(shí)候要用想像力,有時(shí)候半心半意,有時(shí)候以我們自己希望的方式,有時(shí)候以小說要求我們的方式,還有的時(shí)候則需要撥動(dòng)我們生命的所有脈絡(luò)。我在年輕時(shí)曾經(jīng)一度完全鉆入小說之中,看得極為投入——乃至迷狂一般。十八歲到三十歲(1970—1982年)這些年中,我渴望描寫出腦海與心靈中發(fā)生的事情,以畫家繪畫那般的精確和明晰,描繪出豐富復(fù)雜、栩栩如生的景觀,其中有山脈、平原、巖石、森林和江流。 我們閱讀小說的時(shí)候,意識(shí)和心靈之中到底發(fā)生了什么?這些內(nèi)在的感覺與看電影、看油畫、聽詩朗誦或者是史詩吟誦有什么不同?傳記、電影、詩歌、繪畫或童話可以提供給我們的東西,小說也可以時(shí)不時(shí)地提供給我們。但是,小說這種藝術(shù)形式的本真而獨(dú)特的效果,與其他文學(xué)體裁、電影和繪畫相比,具有根本的差異。我或許可以展示這種差異,那就是告訴你們,我在年輕時(shí)狂熱閱讀小說的經(jīng)歷以及內(nèi)心中喚醒的種種復(fù)雜意象。 如果說參觀博物館的人首先希望他所觀看的繪畫給他帶來視覺的愉悅,我則更欣賞景觀里的行動(dòng)、沖突和豐富性。我既喜歡隱秘地觀察某個(gè)人的私生活,也愿意探索廣闊景觀中的黑暗角落。但是,我并不希望讓你以為我心中的圖景總是動(dòng)蕩不安的。我在年輕的時(shí)候閱讀小說時(shí),有時(shí)內(nèi)心會(huì)出現(xiàn)一片寬廣、深遠(yuǎn)而又寧靜的景觀,有時(shí)光線暗淡下去,黑白分明并且相互分離,各種陰影在其中涌動(dòng)。有時(shí)候,我驚詫地感到整個(gè)世界沉浸在一種迥然不同的光芒之中。有的時(shí)候,余暉普照,含攝一切,整個(gè)宇宙化為惟一的情緒和惟一的樣式。我知道,我愛上了這種感覺,我在書中追求的正是這種特別的氛圍。我在伊斯坦布爾貝西克塔什的家中看小說,當(dāng)我慢慢地被吸入小說世界的時(shí)候,我會(huì)意識(shí)到,那些在我打開書頁之前實(shí)際行動(dòng)留下的種種影子——我喝的一杯水,和母親的交談,浮現(xiàn)在心頭的各種想法,懷有的一些輕微怨恨——正慢慢地淡化消逝。 我會(huì)感到我坐的橘色扶手椅、身邊散發(fā)著煙漬味的煙灰缸、鋪有地毯的房間、在街上踢足球互相喊叫的孩子們、遠(yuǎn)處傳來的輪渡汽笛聲正在從我的意識(shí)中遁去,一個(gè)嶄新的世界在我面前正逐詞逐句地展現(xiàn)出來。我一頁接一頁讀下去,這個(gè)新世界就會(huì)越來越具體,越來越清晰,就像那種神秘的繪畫,在倒上試劑的時(shí)候,就會(huì)慢慢顯現(xiàn)出來。各種線條、影子、事件,還有人物進(jìn)入了焦點(diǎn)。在新世界展開的時(shí)刻,任何推延我進(jìn)入其中的事情,任何阻撓我回憶并想像那些人物、事件和物品的事情,都會(huì)讓我煩惱痛苦。一位真實(shí)主人公的遠(yuǎn)親(他們的親緣關(guān)系如何,我已經(jīng)忘記),一個(gè)放著一把槍、不知位于何處的抽屜,或者一次我明知有雙層含義卻說不出另一層含義的談話——諸如此類的事情都會(huì)極度困擾我。在我的目光急切地瀏覽詞句的同時(shí),我的內(nèi)心混合著焦躁和喜悅,希望所有事情馬上各安其位。在這樣的時(shí)刻,我的所有感知之門完全敞開,我就像一個(gè)膽怯的動(dòng)物面對(duì)一個(gè)全然陌生的環(huán)境,我的意識(shí)開始越來越快速地運(yùn)轉(zhuǎn),幾乎到了驚慌失措的地步。我全神貫注于捧在手中的小說的細(xì)節(jié),讓自己與正在深入其中的世界合拍,我會(huì)在想像中努力讓詞語具象化,將書中描寫的所有事物都呈現(xiàn)出來。 過不了多久,這種劇烈的、令人疲倦的思維努力就會(huì)產(chǎn)生結(jié)果,一幅我渴望看到的寬廣景觀在我面前展開,猶如煙霧消散后一片廣袤的陸地,呈現(xiàn)出所有栩栩如生的細(xì)節(jié)。接著,我就會(huì)看到小說敘述的事物,就像有人輕松愜意地臨窗而立,眺望窗外的景色。對(duì)我來說,閱讀托爾斯泰《戰(zhàn)爭(zhēng)與和平》描寫皮埃爾如何在山頂俯瞰波羅底諾戰(zhàn)役是小說閱讀的典型。我們覺得,小說正在將各種細(xì)節(jié)精致地編織在一起,托付給我們;而我們也感到有必要在記憶中集聚這些細(xì)節(jié)。這種細(xì)節(jié)畢現(xiàn)的情形就像面對(duì)一幅畫作,讀者并不覺得是在閱讀小說的詞語,而是在觀賞一幅風(fēng)景畫。在此處,作家對(duì)圖畫細(xì)節(jié)的處理以及讀者通過具象化將詞語轉(zhuǎn)化為大幅風(fēng)景畫的能力,是至關(guān)重要的。我們閱讀的小說并不都是在廣闊的景觀里、戰(zhàn)場(chǎng)上或大自然中展開的,我們也看那些發(fā)生在屋子里的故事,內(nèi)容局限于令人窒息的室內(nèi)氛圍——卡夫卡的《變形記》就是這樣的例子。我們閱讀故事就像在看風(fēng)景,我們的心靈之眼將故事轉(zhuǎn)化為圖畫,努力讓自己融入圖畫的氛圍之中,受其感染,并且實(shí)際上在不斷地追尋它。 讓我舉另外一個(gè)例子,也來自托爾斯泰,描寫的是眺望窗外的行為,可以說明我們?cè)陂喿x時(shí)是如何進(jìn)入小說的景觀之中的。這個(gè)場(chǎng)景出自一切時(shí)代*偉大的小說,《安娜·卡列尼娜》。安娜在莫斯科與弗龍斯基邂逅。晚上乘火車回圣彼得堡的家,她十分快樂,因?yàn)榈诙煸绯烤湍芸吹阶约旱暮⒆雍驼煞颉R韵率切≌f里的場(chǎng)景: 安娜……拿出一把裁紙刀和一本英國(guó)小說。*初她讀不下去。騷亂和嘈雜攪擾著她;而在火車開動(dòng)的時(shí)候,她又不能不聽到那些響聲;接著,飄打在左邊的窗上、粘住玻璃的雪花,走過去的乘務(wù)員裹得緊緊的、半邊身體蓋滿雪的姿態(tài),以及議論外面刮著的可怕大風(fēng)雪的談話,分散了她的注意力。這一切接連不斷地重復(fù)下去:老是震動(dòng)和響聲,老是飄打在窗上的雪花,老是暖氣忽熱忽冷的急遽變化,老是在昏暗中閃現(xiàn)的人影,老是那些聲音,但是安娜終于開始閱讀,而且理解她所讀的了。安努什卡已經(jīng)在打瞌睡,紅色小提包放在她膝上,她那一只手上戴著破手套的寬闊的雙手握牢它。安娜·阿爾卡季耶夫娜讀著而且理解了,但是讀書可以說是追蹤別人的生活的反映,因此她覺得索然乏味。她自己想要生活的欲望太強(qiáng)烈了。她讀到小說中的女主角看護(hù)病人的時(shí)候,她就渴望自己邁著輕輕的步子在病房里走動(dòng);她讀到國(guó)會(huì)議員演說時(shí),她就渴望自己也發(fā)表那樣的演說;她讀到瑪麗小姐騎著馬帶著獵犬去打獵,逗惱她的嫂嫂,以她的勇敢使眾人驚異時(shí),她愿意自己也那樣做。但是她卻無事可做,于是她的小手玩弄著那把光滑的裁紙刀,勉強(qiáng)自己讀下去。 安娜讀不下去,因?yàn)樗恍南胫埶够驗(yàn)樗释睢H绻軌虬阉枷爰性谛≌f上,就會(huì)輕易想像出瑪麗小姐騎上馬,跟在一群獵犬后邊。她就會(huì)具象化那個(gè)場(chǎng)景,好像眺望窗外;她就會(huì)感到自己慢慢進(jìn)入那個(gè)她自己正從外部觀察的場(chǎng)景之中。 大多數(shù)小說家感到,閱讀小說的開始幾頁就像進(jìn)入一幅風(fēng)景畫。我們來回憶一下斯湯達(dá)是如何開始寫《紅與黑》的。我們首先從遠(yuǎn)處看到了維里業(yè)小城,看到了它所在的山坡,蓋著尖尖的紅瓦屋頂?shù)陌咨孔樱粎矃裁苠賱诺睦踝訕洌潜さ膹U墟。杜河在城堡下流淌。接著,我們看到鋸木廠和生產(chǎn)印花布的工廠。 在接下來的一頁,我們就已經(jīng)遇到了作為中心人物之一的市長(zhǎng),并了解了他的性格。閱讀小說的真正快樂在于可以不用從外部,而是直接從生活在小說世界的主人公眼中觀看那個(gè)世界。閱讀小說時(shí),我們?cè)陂L(zhǎng)遠(yuǎn)的視野和飛逝的時(shí)光之間穿梭,在普遍的思想和特殊的事件之間游走,速度之快非其他任何文學(xué)體裁可以賜予。我們注目觀看遠(yuǎn)處的風(fēng)景畫之時(shí),會(huì)恍然發(fā)現(xiàn)我們自己已經(jīng)進(jìn)入了畫中人物的思想世界,發(fā)現(xiàn)了人物情緒的細(xì)微變化。這與觀賞中國(guó)山水畫的體驗(yàn)是相似的。畫中有一個(gè)不大的人形置身于巉巖、江水與枝葉婆娑的樹林之間:我們注視著他,并試著從他的眼光想像周圍的風(fēng)景。(中國(guó)畫應(yīng)該以這種方式來觀賞。)于是,我們意識(shí)到,景觀的布局是為了反映畫中人物的思想、情緒和感知的。由此類推,我們就明白了,小說里的景觀是小說主人公內(nèi)心狀態(tài)的延伸和組成部分。我們會(huì)意識(shí)到,通過一種無縫的過渡,我們已經(jīng)與這些主人公融為一體。閱讀小說意味著,在把整個(gè)情境納入記憶之時(shí),我們亦步亦趨地跟隨著主人公的思想和行動(dòng),并在總體景觀中給這些思想和行動(dòng)賦予意義。我們現(xiàn)在進(jìn)入了小說的景觀之中,而不久之前我們還是在外圍打量:我們除了在心靈之眼中看到了山脈,還感受到了河水的清涼,嗅到了樹林的味道,與主人公交談,進(jìn)入到小說宇宙的深處。小說語言幫助我們?nèi)诤线@些相隔遙遠(yuǎn)、判然有別的元素,讓我們看到在統(tǒng)一的圖景之中主人公們的面孔和思想。 我們沉浸在小說中的時(shí)候,我們的意識(shí)在緊張地工作,但并不像安娜那樣。她在開往圣彼得堡的、頂著白雪的、嘈雜的火車上看書,心中卻另有所想。我們不斷巡逡于景觀、樹林、人物、人物思想以及他們觸摸過的物品之間——從物品,到物品引發(fā)的記憶,到別的人物,再到一般的思想。我們的意識(shí)和感知在猛烈地運(yùn)轉(zhuǎn),全神貫注,風(fēng)馳電掣,同時(shí)還執(zhí)行著許許多多的操作。但是我們?cè)S多人甚至并不知道自己在執(zhí)行這些操作,就像司機(jī)在開車的時(shí)候,并不知道自己在掛擋、踩剎車、小心翼翼地轉(zhuǎn)方向盤,同時(shí)也遵守著許多規(guī)則,閱讀并理解著各種道路標(biāo)志,判斷著交通狀況。 上述關(guān)于司機(jī)駕駛的類比對(duì)讀者和小說家同樣有效。有些小說家并沒有意識(shí)到自己采用的技巧。他們率性地寫作,仿佛在執(zhí)行一個(gè)完全自然的行為,并不知道腦海中運(yùn)行的種種操作和估算,不知道他們事實(shí)上正在使用小說藝術(shù)賦予他們的各種齒輪、剎車器和掛擋桿。讓我們用“天真的”一詞來形容這種心智類型,這類小說家和讀者——他們根本不關(guān)心寫作和閱讀活動(dòng)的人為層面。另外,我們還可以用“反思的”一詞以形容正好相反的心智類型:換言之,那些讀者和作家明知文本的人為性,明知文本不等于現(xiàn)實(shí),但卻一樣沉迷其中,他們關(guān)注小說寫作的方法以及閱讀小說時(shí)意識(shí)活動(dòng)的方式。作為小說家,就要同時(shí)掌握天真的與反思的藝術(shù)。 或者說,既是天真的,也是“感傷的 ”。弗雷德里希 ·席勒在其著名論文《論天真的詩和感傷的詩》(über naive undsentimentalische Dichtung,1795— 1796)中首次提出了這對(duì)術(shù)語。在席勒的論述中,德語“sentimentalisch”形容那種沉郁而又痛苦的現(xiàn)代詩人,他已經(jīng)喪失了孩提的天真和秉性,這與英語對(duì)應(yīng)詞“sentimental”的意思不盡相同。不過,我們不用糾纏于具體意思。實(shí)際上,席勒受勞倫斯·斯特恩《感傷的旅行》的啟發(fā),從英語借用了該詞。(席勒充滿敬意地把斯特恩加入天真的孩提般天才的行列,其中還包括但丁、莎士比亞、塞萬提斯、歌德,甚至丟勒。)我們只需要知道,席勒使用該詞表示那種偏離了自然的簡(jiǎn)樸與力量,過分沉迷于自我的情緒和思想的意識(shí)狀態(tài)。我從年輕時(shí)起就非常喜愛席勒的這篇論文,在此我打算探尋對(duì)該文更深刻的理解,通過該文闡明我自己關(guān)于小說藝術(shù)的思想(我一直在這么做),并且做到精確的表述(恰如我現(xiàn)在努力要實(shí)現(xiàn)的)。托馬斯·曼認(rèn)為席勒的著名論文是“德語*雅的文章”。席勒把詩人分為兩類:天真的與感傷的。天真的詩人與自然融為一體;實(shí)際上,他們就像自然——平靜、無情而又睿智。他們率真地寫詩,幾乎不假思索,不會(huì)顧慮其文字的理智的或倫理的后果,也不會(huì)理睬別人的評(píng)論。相比于同時(shí)代的詩人,他們認(rèn)為詩就是自然賦予的一個(gè)有機(jī)的印象,這印象從未離開他們心田。天真的詩人是自然造化的一部分,詩從自然造化而來自發(fā)地流入天真詩人的筆端。詩不是詩人思考出來的,不是詩人處心積慮創(chuàng)作的成果,不需要表現(xiàn)于某種既定的格律之中,也無需不斷的修改和自我批判;詩應(yīng)該不加反思地就流出筆端,詩甚至可能是獲得了自然、神或者其他某種力量的啟示。宣揚(yáng)這種浪漫主義觀念的還有英國(guó)詩人柯勒律治。他是德國(guó)浪漫派的忠實(shí)追隨者,在1816年《忽必烈汗》一詩的序言中,他明確表達(dá)了上述思想。(我的小說《雪》主人公詩人卡,就是在柯勒律治和席勒的影響下創(chuàng)作詩的,并且同樣堅(jiān)持天真詩的觀念。)每次閱讀席勒的論文總會(huì)激起我無比的敬佩之情。他所說的天真詩人擁有一個(gè)決定性的秉性,我希望特別加以強(qiáng)調(diào):天真詩人毫不懷疑自己的言語、詞匯和詩行能夠描繪普遍景觀,他能夠再現(xiàn)普遍景觀,能夠恰當(dāng)并徹底地描述并揭示世界的意義——因?yàn)檫@個(gè)意義對(duì)他來說既非遙不可及,也非深藏不露。 在另一方面,席勒認(rèn)為,“感傷的”(多情的、反思的)詩人至少在一個(gè)方面可以說是忐忑不安的:他不確定他的詞語是否涵蓋了真實(shí),是否可以達(dá)到真實(shí),不知道他的表述是否傳達(dá)了他追求的意義。因此,他極度關(guān)注自己寫的詩,關(guān)注所使用的方法和技巧以及自己努力運(yùn)用的策略。天真詩人并不詳細(xì)區(qū)分他所感知的世界與世界自身,但是,感傷——反思性的現(xiàn)代詩人質(zhì)疑自己感知到的一切事物,甚至質(zhì)疑自己的感覺本身。當(dāng)他把自己的感知鑄入詩行的時(shí)候,他會(huì)考慮許多教育的、倫理的與理智的原則。 對(duì)那些愿意思考藝術(shù)、文學(xué)與生活之間關(guān)系的人來說,席勒的這篇我認(rèn)為非常有趣的、著名的論文是一個(gè)引人入勝的源泉。我年輕時(shí)一遍又一遍地讀它,思考它所提供的事例、評(píng)論的詩人,以及率性創(chuàng)作和在理智的幫助下有自我意識(shí)的努力創(chuàng)作之間的種種差異。我閱讀這篇論文,當(dāng)然也會(huì)反思作為小說家的我自己以及我在寫小說時(shí)體驗(yàn)到的各種情緒。我想起自己在從事小說創(chuàng)作之前作畫的感受。從七歲到二十二歲,我在畫畫時(shí)一直夢(mèng)想著有一天成為一名畫家,但是我的畫作從沒有擺脫天真氣,后來我就放棄了繪畫,也許是在我明白了這一點(diǎn)之后。也是在那時(shí)候,我想為什么席勒將藝術(shù)和文學(xué)稱作*普遍意義上的“詩”。在本系列講座中,我還將思考同樣的問題,以遵循諾頓講座的精神和傳統(tǒng)。席勒的這篇內(nèi)容豐富、引人深思的文章將會(huì)伴我思索小說的藝術(shù),讓我想起自己年輕時(shí)的創(chuàng)作之路如何謹(jǐn)慎地在“天真”與“感傷”之間徘徊。 席勒的論文不只是關(guān)于詩的,或者僅僅是關(guān)于普遍的藝術(shù)和文學(xué)的,在某些地方其實(shí)是關(guān)于人性類型的哲學(xué)文本。這些內(nèi)容直指戲劇和哲學(xué)的*,我喜歡閱讀字里行間的個(gè)人思想和觀點(diǎn)。席勒說:“人性有兩種不同類型。”意思是說,根據(jù)日耳曼文學(xué)史,“那些天真者如歌德,那些感傷者如我自己!”席勒嫉妒歌德,不僅因?yàn)楦璧碌脑姼璺A賦,而且也因?yàn)楦璧伦孕牛患偎螅瑢庫o雍容,不矯揉造作,有貴族氣派;因?yàn)楦璧虏毁M(fèi)雕琢就可以傾吐偉大燦爛的思想;因?yàn)樗心芰Ρ憩F(xiàn)自我;因?yàn)樗暮?jiǎn)約、謙遜和天才;還因?yàn)樗静恢肋@一切,恰似一個(gè)孩童之所為。相反地,席勒本人則多思和理智,文學(xué)創(chuàng)作活動(dòng)更為糾結(jié)和痛苦,清醒知道自己的文學(xué)方法,對(duì)這些方法的可靠性持懷疑態(tài)度——并且感到這些態(tài)度和特點(diǎn)更為“現(xiàn)代”。我三十年前閱讀《論天真的詩和感傷的詩》的時(shí)候,我也——就像席勒對(duì)歌德發(fā)怒——對(duì)上一代土耳其小說家們天真幼稚的風(fēng)格滿腹牢騷。他們寫起小說來如此輕松,從不擔(dān)心風(fēng)格與技巧的各種問題。我不僅把 “天真的”一詞(我當(dāng)時(shí)傾向于使用其否定性的意思)加到他們頭上,也加給全世界所有把19世紀(jì)巴爾扎克式小說當(dāng)做理所當(dāng)然的作品、不加質(zhì)疑地接受的那些作家。現(xiàn)在,在經(jīng)歷了三十五年的小說創(chuàng)作歷險(xiǎn)之后,我愿意繼續(xù)以身說法,并且努力說服自己相信,在內(nèi)心找到了天真小說家和感傷小說家之間的平衡。
天真的和感傷的小說家 作者簡(jiǎn)介
奧爾罕·帕慕克(Orhan Pamuk,1952- ),當(dāng)代歐洲*杰出的小說家之一,享譽(yù)國(guó)際的土耳其文學(xué)巨擘。出生于伊斯坦布爾,曾在伊斯坦布爾科技大學(xué)主修建筑。2006年獲得諾貝爾文學(xué)獎(jiǎng),作品總計(jì)已被譯為50多種語言。 其他作品: 《我的名字叫紅》《白色城堡》《伊斯坦布爾:一座城市的記憶》《雪》《黑書》《新人生》《寂靜的房子》《杰夫代特先生》《純真博物館》《別樣的色彩》
- >
我與地壇
- >
隨園食單
- >
史學(xué)評(píng)論
- >
伊索寓言-世界文學(xué)名著典藏-全譯本
- >
企鵝口袋書系列·偉大的思想20:論自然選擇(英漢雙語)
- >
有舍有得是人生
- >
詩經(jīng)-先民的歌唱
- >
月亮與六便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