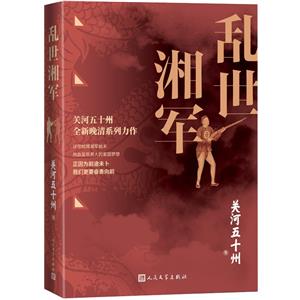-
>
一個陌生女人的來信:茨威格短篇小說集
-
>
女人的勝利
-
>
崇禎皇帝【全三冊】
-
>
地下室手記
-
>
雪國
-
>
云邊有個小賣部(聲畫光影套裝)
-
>
播火記
亂世湘軍 版權信息
- ISBN:9787020111657
- 條形碼:9787020111657 ; 978-7-02-011165-7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亂世湘軍 本書特色
關河五十州 全新晚清系列力作 詳盡梳理湘軍始末 熱血呈現男人的家國夢想 正因為前途未卜 我們更要奮勇向前
亂世湘軍 內容簡介
《亂世湘軍》是關河五十州全新的歷史小說,小說沿著湘軍從*初的雛形到正式組建及至發展壯大的時間脈絡,通過一系列著名的戰役詳盡再現了湘軍波瀾壯闊的歷史始末以及一個個熱血將領的生動形象。比如組建了湘軍雛形的楚勇將領江忠源,蓑衣渡一戰,他僅憑區區千人,差點全殲天平天國全部兵力;比如采用兩地打援策略的胡林翼;比如讓田平軍聞風喪膽的孤膽英雄鮑超;還有孔武勇猛的都興阿,等等。所有這些將領在一次次的軍事行動中漸漸展現出不同的性格特點,同時又合為一個整體把湘軍能征善戰、有勇有謀、敢拼敢沖的特點表現得淋漓盡致。 《亂世湘軍》不僅展示了激蕩人心的一場場戰役,同樣也靜心梳理了每一場戰役得失成敗的經驗,關于戰爭的書寫中,處處體現出關于謀略的分析和人性的探究。說到底,所有的事情都與人有關。關河五十州試圖通過詳盡史料的梳理,盡量不帶偏見地還原曾經的硝煙與戰火、光榮與夢想。歷史的進程,一度是在無數無名兵勇的卓絕戰斗中,緩緩向前的。這樣的書寫態度,是對那些曾經熱血奮戰的人,*好的體諒與尊重。
亂世湘軍 目錄
目 錄
**章 另外一條道路
第二章 初生牛犢不怕虎
第三章 大比拼
第四章 轉折點
第五章 攻敵所必救
第六章 釜中游魚
第七章 一代新人換舊人
第八章 血淋淋的現實
第九章 曙光就在前方
第十章 惡 戰
第十一章 血流成河
第十二章 兵臨城下
第十三章 歷史的盡頭
亂世湘軍 節選
**章另外一條道路 1851年4月,大學士賽尚阿以欽差大臣的身份被派往廣西,用以遏制已如同火山噴發一般的太平天國運動。出發前,內閣中書左宗植建議賽尚阿,應在其班子中加入一個名叫江忠源的人;無獨有偶,另一位大學士祁雋藻也向賽尚阿推薦了江忠源。 賽尚阿當時對江忠源并不了解,只知道他是舉人出身,做過地方小官;但既然兩名同僚都不約而同地推薦了他,又都認為此人是一員不可多得的干才,于是便奏準讓江忠源隨營辦差。幾個月后,江忠源前往賽尚阿位于桂林的行轅報到,賽尚阿將他調入了廣州副都統烏蘭泰的軍幕。 那個時代人們的刻板印象是,滿人尚武,漢人崇文。后者似乎已成為漢人的專利,他們滿腹經綸,卻通常手無縛雞之力。烏蘭泰就是有過從征回疆經歷的滿洲軍人,從沒有讀書應試;江忠源出身舉人,自然也應該是個文弱書生才對。實際不然,江忠源能文能武,而且言談舉止都極為豪爽干練,這讓烏蘭泰很是高興。兩人相處融洽,彼此都覺得十分投機。經過進一步了解,烏蘭泰才知道,江忠源原來也和他一樣打過仗,而且仗還打得非常漂亮。 “古兵法”之策 在江忠源的家鄉湖南新寧,一度會黨活動非常頻繁,先后爆發了雷再浩、李沅發起義。其時太平天國運動尚未形成氣候,湖南省官員擬調大部隊去新寧鎮壓,但被江忠源勸止。 官軍是客軍,不熟悉新寧的當地情況,難以對付本地義軍不說,還會騷擾民間。江忠源回到新寧,依托家族子弟,建立了名為新寧勇的團練;自己教兵勇兵法,然后指揮他們與義軍作戰。結果竟得以一戰討平,江忠源也因此嶄露頭角。 至此,烏蘭泰終于明白,為什么京城大吏會紛紛推薦江忠源了。這時新寧勇早已遭到遣散,但烏蘭泰仍力勸江忠源重建部隊,拉到廣西來打太平軍。江忠源聽從其言,即刻寫信給正在家鄉的四弟江忠淑。江忠淑的動作也很快,立馬招募了五百人開進廣西,號為“楚勇”。楚勇原先由江忠淑直接帶隊,由于江忠淑身患痢疾而提出辭呈,便改由江忠源親自指揮。 在廣西集結的各路清軍中,只有楚勇以省命名。雖然該部的五百兵勇仍舊保留著其鄉勇的特色,但與原先的新寧勇相比,部隊建制已升級成為更高形式——新寧勇是地方團練,自衛鄉里,自籌經費,作戰范圍連新寧都不出,更別說出境來廣西了。楚勇至少是準正規軍,不僅跨鄉跨省,而且和經制兵綠營一樣,由官府供餉。 隨賽尚阿征戰的部隊,多為從各省抽調的正規軍。起先他們尚看不起楚勇,楚勇普遍身材短小、衣衫不整的樣子也成為其笑料;然而戰場之上,歸根到底不是看誰的形象好,而是看誰更能打。幾次交戰下來,楚勇用實際表現證明了他們絕非浪得虛名,其他官軍漸漸也就不敢再小視他們了。 賽尚阿定下封鎖戰略,企圖將太平軍困死在狹小的紫荊山區。不料太平軍卻突圍東出,攻克了山城永安,隨后便在永安封王建制,擴大隊伍。 1851年歲末,賽尚阿督令各部對永安予以四面合圍。賽尚阿倚重的大將,除了烏蘭泰外,尚有廣西提督向榮。偏偏烏蘭泰與向榮不和,江忠源欲為他們居中調解,卻毫無成效。 包圍永安時,烏蘭泰與向榮之間再次發生齟齬。向榮提出“古兵法”之策,所謂“古兵法”,就是圍三闕一,假意給被圍的太平軍留出一條逃生之路,繼而予以半路截擊。烏蘭泰則指出,永安城中的太平軍如今連一萬都不到,清軍數倍于敵,只要堅持圍攻下去,就算攻不進城,光是餓,都能把太平軍給餓死。 圍三闕一的打法,通常都要在守軍意志接近崩潰邊緣的情況下,才能順利實施。太平軍卻不是這樣,通過永安封王,其作戰意志空前高漲,換句話說,只要給他們一個空隙,他們便會像錐子一樣拼命地鉆出去;而以清軍的狀態和戰斗力,屆時十之八九,是既截不住,也追不上。反之,若繼續圍困,守軍意志再強,也將一點點被消磨。事實上,由于內外不通,接濟斷絕,城內太平軍的糧食已經所剩無幾,火藥也用完了,這意味著他們能夠守住永安的時日,已經在倒數計算。江忠源看出了太平軍的困境,他站在烏蘭泰一邊,并代烏蘭泰寫信給向榮,力陳“古兵法”之弊,請求大家同心協力,合圍殲敵,但未被向榮所接受。 向榮把他的“古兵法”獻給賽尚阿,賽尚阿急于向朝廷報捷,便采納了他的建議。到了這個時候,江忠源已預感到清軍必敗,自己留在軍中也無能為力;同時他對各部官軍皆畏縮不前,且又無法當機立斷、協同作戰的作風也深感失望,于是便稱病告退,帶著楚勇返回了新寧。 不出所料,正是借助向榮“古兵法”留出的缺口,太平軍雨夜突襲,強行沖出了包圍圈。清軍失去了將太平軍扼殺于其創業初期的*好也是*后一次機會。 永安突圍后,太平軍浩浩蕩蕩北上,直逼桂林。接下來,太平軍必然還要繼續北上進入湖南乃至新寧。這次不用官方督促和征召,江忠源便散盡家財,捐資募勇一千兩百人,于一個月內馳援桂林;又囑咐三弟江忠濟和同縣好友劉長佑等人,再添募五百人,隨后跟進。就在抵達桂林之前,江忠源聽到一個消息:烏蘭泰率部追擊太平軍,但在桂林城外負傷斃命。 太平軍真是既可怕又可恨,江忠源傷感不已。他知道,自己即將迎來的戰斗將更為艱難和兇險,面對這一從未有過的挑戰,他必須全力以赴,使出渾身解數才行。 蓑衣渡 太平軍向桂林挺進,意味著他們即將沖出兩廣,進入相對富足的長江流域。因此在攻桂林未果后,他們便立即撤圍改攻全州,占領全州后,不待休整,又準備先取長沙,再圖武昌。 出發前,南王馮云山依據情報得知,全州城東北有個湘江渡口,名為蓑衣渡,乃必經之地。此處江面狹窄,水流湍急,行船十分危險,同時兩岸又多山林,如果清軍提前扼奪,足以置太平軍于死地。馮云山向天王洪秀全建議,在經過蓑衣渡時,應派步兵在兩岸先行開道,其余部隊、家眷和輜重則乘船隨后跟進。 此時湘江上漲,預計順流而下的話,三四天內即可抵達長沙。馮云山的做法,穩妥當然是穩妥了,但時間也被延誤了。若要是這一期間,讓長沙方面做好防守準備,豈不是會竹籃打水一場空?洪秀全仍決定全軍都乘船走水路,并打算率船隊先行。“蓑衣渡是極險惡的地方,倘有不測,后果不堪設想,老弟我愿意先行進入。”馮云山在攻打全州時,已經中炮負傷,但仍請纓擔任了前隊指揮。 正如馮云山所預料的,有人已經在蓑衣渡設伏了,此人就是江忠源。 江忠源從桂林起,就尾隨太平軍,一直跟到全州。發現全州已被太平軍所控制,他趕緊繞到前面,以切斷太平軍向北延伸的通道。蓑衣渡由此被江忠源所選中,他對蓑衣渡的地形進行了周密偵察:蓑衣渡就渡口而言,實際水波平靜,真正的險要的地段在其北面三里許,名為水塘灣。水塘灣也屬于蓑衣渡區域,其西岸有沙灘突出江面,河床極為狹窄,兼之湘江在此急轉向東,故而江水雖然不深,水流卻極為湍急,船只很難通行。 水塘灣的岸邊大樹參天,無數灌木錯落其間,江忠源伐木塞河,打樁設阻,預先攔住了河道。太平軍的先頭船隊在進入水塘灣后,先順著湍急的江水駛過淺灘,繼而在河曲處轉了個彎,接著便直直地沖入由巨木和木樁組成的障礙區并發生擱淺。 江忠源率楚勇埋伏在附近的獅子山,四處揮舞旗幟作為疑兵。太平軍不知虛實,急忙撤退,可是因水流湍急,船隊已無法做到進退自如:前面的船退不出來,后面的船也停不下來,結果越擠越多,全都撞在了一起。楚勇趁機以火炮進行襲擊,一時間,炮子(即炮彈)、火箭如同雨點一樣落在船上,隨著大火在船只之間迅速蔓延,船隊更加混亂不堪。很多船只或自相撞擊,或沉沒,或被焚,其間不少人被溺死、燒死、轟死。 在無法拔樁搶渡的情況下,馮云山指揮前隊棄舟登岸,向楚勇發起反擊。太平軍準備不足,在地形上處于絕對劣態;而楚勇卻以逸待勞,居高臨下,并且牢牢地將對手置于其火力射擊范圍之內。激戰半天,太平軍被一路趕殺,重又退回江中。 楚勇處于西岸,太平軍可以先退至對面的東岸;但東岸同樣地形復雜,亦可能藏有大量伏兵,對于已陷入困境的太平軍而言,這種風險更加難以預測和控制。馮云山只能繼續傾全力在西岸進行爭奪,而江忠源既然已經緊緊咬住了對手,當然也不肯輕易松口,雙方連續拉鋸達兩個晝夜。 由于前隊遲遲無法打開局面,洪秀全遂率后隊助陣。江忠源在獅子山上看到太平軍的后隊旗幟,已準備撤離;就在這個時候,炮子忽然打到了馮云山的船上,馮云山再負重傷。隨著馮云山失去指揮能力,船隊大亂,洪秀全不得不下令拋棄所有船只和輜重,全軍登上東岸。馮云山被抬到東岸后,很快就因傷重不治而亡。洪秀全當場慟哭,說:“是老天不肯讓我平定天下嗎?為什么這么快就奪走了我的賢良輔弼?” 永安封王,馮云山雖然僅僅被封為南王,位列東王楊秀清、西王蕭朝貴之后,但他實際卻是太平天國領導層的核心人物。太平天國起事,醞釀數載,皆馮云山一人之謀。作為領袖的洪秀全對其尤為依賴,平時只要遇到疑難,就一定要問馮云山;而足智多謀的馮云山,也總是能靠一兩句話就解決問題,以至于洪秀全幾乎寸步都不能離開他。 早在紫荊山區時,馮云山的地位和影響就已無人可及;太平天國的其他領導人,從楊秀清、蕭朝貴到韋昌輝、石達開等,都是由他捏合在一起的,也對他衷心擁戴。有研究者認為,如果馮云山不是死于蓑衣渡之役,他完全可以繼續輔佐天王,裁制東王,調和各王,后來的天京內訌也許就不會發生了。 首功 關于馮云山之死,一直以來,還有另外一種說法,即認為他在進攻全州時就已戰死,這一說法近年來已逐漸被研究者所排除。之所以會出現不一樣的說法,很大程度上,與江忠源當時不知馮云山已死有關。在事后的報告中,他對此只字未提,相應官書乃至地方縣志便也都沒有做相應記載。 江忠源提及的,主要是鏖戰兩晝夜,繳獲船只三百余和大量輜重,以及極大地殺傷了太平軍精銳。這是事實,蓑衣渡一役,太平軍戰死數千人,陣亡者多數是原來紫荊山區的拜上帝會會眾,普遍具有強悍善戰和忠心天國的特點,乃太平軍不可多得的精銳火種,對太平天國政權而言,如此損失是很難彌補的。 江忠源人馬有限,戰前他曾請求官軍協同行動,在湘江東岸進行伏擊。東岸重山疊嶂,僅有羊腸小道可以通行,如果官軍也像楚勇一樣在那里建立陣地,幾乎可以確定太平軍插翅難逃,*終將全軍覆沒于蓑衣渡。可是顯然,官軍并沒有把江忠源的請求當一回事,楚勇在蓑衣渡連戰兩日,官軍竟無一人增援,東岸更是空無一人。 在馮云山死后,太平軍已沒有選擇,只能舍船由東岸登陸;而東岸的不設防,則給了他們逃出生天的機會。洪秀全率部穿過東岸林木郁密的山丘,徒步進入了湖南。他們本欲通過攻占臨河的商業重鎮永州,獲取新的船只和給養,但由于官軍已截斷橋梁,船只也已被拖至對岸,所以便放棄永州,向南折往道州。對于太平軍的突然轉向,道州守軍完全缺乏準備,防衛形同虛設,結果被太平軍輕易攻取。 江忠源在蓑衣渡設伏的主要目的,是塞斷太平軍北進湖南的水陸通道。在伏擊成功后,他曾一度認為,太平軍將鎩羽南返,湖南可能已經守住;太平軍攻占道州,使他的這一希望破滅了。盡管*終未能阻遏太平軍北進湖南,但蓑衣渡一戰卻已實質性地保住了長沙甚至湖南。 太平軍的本意是經湘江直接對長沙發動快攻,其時長沙防備空虛,兵力又少,一旦太平軍迅疾發動攻擊,被攻下的概率極高。可是因為落敗蓑衣渡,太平軍被迫改變了行進方式和路線,快攻長沙的計劃也被迫延遲。此外,他們不僅要重整士氣,還要招募兵員和補充給養,以彌補蓑衣渡之戰的重大損失,這使他們在道州和湘南其他地區又耗去了不少寶貴的時間。 沒有蓑衣渡一戰,長沙可能早就被太平軍攻克了,湖南自然也將在其掌握之中,故而此戰“為保全湖南首功”。當時很多人認為,“天下不可一日無湖南”,從后來湖南的戰略地位來看,也確實如此:設若湖南盡入太平軍之手,則太平軍可盡收湖南精兵,順江而下,占領南京;北伐也因此可能提前,在各處對太平軍都還缺乏戒備的情況下,整個戰局必將發生急劇變化。 經過蓑衣渡一役,江忠源的聲名與日俱增,其知兵善戰之譽,在湘省無人能及。他自己也因功升為知府。 大家都知道江忠源能打仗,但是他的話還是沒人聽。太平軍剛剛占據道州時,兵猶不滿萬人;江忠源提出“分防不如合剿,遠堵不如近攻”,也就是說應合兵一處,直接奔赴道州開打。這本是消滅太平軍的上策,結果愣沒人搭理,湘南諸城也相繼被太平軍各個擊破。 通過在湘南流動作戰,太平軍又增加了五萬人馬。在太平軍內部,西王蕭朝貴被評價為“勇敢剛強,沖鋒**”,他通過諜報,得知長沙仍空虛無備,便向總籌軍務的東王楊秀清請命,欲突襲長沙。楊秀清認為蓑衣渡戰役后,已失去突襲的時機,沒有同意;洪秀全也持同一意見。蕭朝貴倔勁上來,帶上僅千余人的部隊,就自顧自地長驅直入,對長沙發動突襲。 1852年9月12日,蕭部直抵長沙城下。由于其余太平軍仍停留在湘南,尚無會攻長沙的跡象,所以蕭朝貴的猛襲,可以說是完全出乎人們的意料。城內居民甚至都還不知道一場大戰即將來臨,直到太平軍發炮攻城,炮子打到城中,街上賣漿的小販正要拿碗來喝,炮子的碎片恰好將碗擊得粉碎,百姓這才驚慌起來。 省城面臨的危機 至蕭朝貴襲擊長沙時,官軍采取的實際仍是分防和遠堵策略,部隊大多還部署在別的地方,城中守軍的數量有限。不過蕭朝貴得到的情報也并不準確,這時距蓑衣渡之戰已經過去了三個月,官府各種嚴防死守的措施都已實施,蕭朝貴要想在短時間內予以攻取,是很難做到的。 在此之前,江忠源按照劉長佑的建議,從楚勇中挑選五百人組成敢死隊,準備在關鍵時刻應急。得知長沙被圍,江忠源忙率敢死隊火速馳援長沙。如果再加上總兵和春等其余援軍,長沙清軍的數量已是蕭部的數倍。但與包圍永安時的情況相仿,官軍多不中用,真正驍勇能戰的,仍然只有江忠源及其楚勇,故而要想一舉擊潰太平軍,也等同于天方夜譚。 蕭朝貴兵力單薄,無法對長沙進行合圍,便集中兵力于南門外,做出準備打持久戰的架勢。江忠源察看形勢,發現南城外的蔡公墳地勢較高,若任由太平軍占據,對城門的威脅很大,于是便發動急襲,將其拿了下來。 蕭朝貴被扼住要害,使不出勁來,只能靠蠻力拼命攻城。他身穿黃色官袍,天天在**線督戰,目標極為顯眼;城中守軍懷疑他就是西王,一炮打過來,蕭朝貴中彈,隨即傷重斃命。 蕭朝貴死后的第三天,曾國藩回到了家鄉——湖南湘鄉荷葉塘。曾國藩和江忠源是湖南同鄉兼好友。咸豐皇帝剛剛登基時,曾國藩應詔保舉賢才,江忠源就在其保舉名單之上。不久因江父去世,江忠源丁憂回籍,才沒有入京為官。 在賽尚阿奉旨攻打太平軍之初,曾國藩對于前景還抱著極為樂觀的態度:在他看來,紫荊山區的太平軍已是釜中之魚,只要賽尚阿統大軍發動進攻,就能一舉將其殲滅。誰料后來情況越來越不對了,已經進了鍋的“魚”居然又跳出來,而且越蹦越歡實。曾國藩對此又氣又急,埋怨前線辦差人員不得力,恨不得自己馬上插手才行。曾國藩曾經兩次兼任兵部侍郎,軍事知識是有一些的,但那都得自于書本,他自己還從未打過仗。曾國藩對此倒也頗有自知之明,知道在京城空發議論,并不能代替親自到前線實踐,所謂“軍事非親臨其地難以遙度”。 就在太平軍轉道湘南期間,曾國藩充任江西鄉試正考官,并獲準于鄉試結束后回籍省親。途經安徽境內時,母親江氏突然病故,兇信傳來,曾國藩急忙按照丁憂的通例,辭去官職,然后溯江西上,回家奔喪。曾國藩雖然沒有參加長沙戰役,但比之于京城,戰火無疑離他已經近得不能再近了——長沙吃緊,湘鄉也吃緊;長沙緩和,湘鄉亦緩和。 蕭朝貴的死,并沒有能夠從根本上解除省城面臨的危機。洪秀全得報,既驚又怒,立即率全軍北上,直指長沙。江忠源率楚勇前去堵截,部隊先勝后敗,實際是中了太平軍的誘兵之計,被伏擊了。江忠源本人被長矛刺中后,墮下馬來,險些喪命。 你在蓑衣渡給了我一悶棍,我現在也姑且還些利息給你!太平軍復仇心切,很快就得以兵抵長沙,對城池形成了重圍之勢。此時,朝廷從各方緊急調集的援兵都已陸續抵達。雙方參加的兵力均達到五萬以上,從而使長沙會戰升級成為超十萬兵員規模的大戰役。 清軍雖然在數量上還多于太平軍,但質量方面卻遠不如對方。從外地趕來的大多數援軍都停留在數里之外,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誰也不敢貿然進發,都怕被太平軍給一口吃掉。這樣一來,太平軍便可以從容攻城了。 長沙城和太平軍先前圍攻的桂林城相似,都具有墻高城堅的特點,對于這樣的堅城,傳統的攻城工具,如云梯、呂公車等,均無能為力。即便是當時的火器,無論是國內自制的銅炮、鐵炮,還是從國外進口的洋鐵炮,也都不具備直接擊破城墻的能力。如此一來,便只有掘開地道,埋地雷攻城一法了,古代軍事學中謂之“穴地攻城”。 還在發動金田起義時,就有貴縣銀礦工人加入了太平軍,他們一般不直接參加作戰,而是專任掘地道作業。太平軍將掘地道攻城稱為“開龍口”,作業人員為“開龍口兄弟”。“開龍口”一詞,就是當時貴縣銀礦工人常說的術語。 太平軍進攻桂林,曾在城門外掘地道。但因桂林城根多堅石,花了一個多月時間也沒能挖成,大軍只得撤圍北出。此后在全州攻城時,再次嘗試,終于得以成功:全州城墻被炸開兩丈余,部隊得以從缺口處一擁而入。 太平軍在湘南進行休整和擴軍期間,又有數千掘煤工人參軍,加上原有的銀礦工人,他們被正式組成了一個新的兵種——土營。土營相當于現代的工程兵特種部隊。中國古代不乏地道戰的記錄,明清兩代都有采用;但像這樣采用整建制部隊的形式,還從來沒有過。由此也可見太平軍用兵靈活高效、不拘一格的特點。 地道戰 所謂埋地雷攻城,其實是在城腳堆滿火藥,然后點燃引信,靜候轟裂。太平軍在湘南時積蓄了大量的火藥,只要挖通地道,轟城就沒有問題。 戰場從來是自覺性要求*高的課堂。清軍在經歷桂林、全州兩戰后,對于地道戰也早有防范,并制定了具有針對性的方案。當土營在城墻邊挖掘地道時,城內守軍便將大木桶埋到地里,讓提前物色好的盲人鉆在桶里,細聽遠處挖掘地道的聲音。盲人聽覺特別敏銳,可以準確地判斷出地道已經挖到何處。一旦發現地道已接近完工,守軍就要用大鐵球將其壓垮;或者是將其砸開后,通過灌水、灌糞,將正在施工中的土營官兵逼走。 太平軍當然也想到了守軍可能使用的辦法,他們在城墻外不斷擊鼓,用以擾亂盲人的聽覺,但成效并不明顯。在長沙會戰中,太平軍一共挖了十個地道,*后只有三個地道先后得以完成。 三個地道均被太平軍充分利用,他們引爆火藥,通過炸毀的城墻進行突破。這時候守軍便要像堵大堤的缺口一樣,全力進行封堵。江忠源參加了反地道戰的全過程,并親身封堵過一次,他在經歷各種驚心動魄場面的同時,也積累了反地道戰的經驗以及技術。 太平軍的地道屢挖不成,三次突破也都未能成功。接著,軍中又開始缺鹽,洪秀全被迫決定撤圍。在雙方大軍都已齊集,且咬合在一起的情況下,一方突然撤出戰場,一般而言,是比較危險的。江忠源已經考慮到太平軍如果撤圍而走,必須如何截殺的問題。在軍事會議上,他指出來援的官軍集結于周圍,唯有西面空虛,希望能調重兵駐扎于湘江西岸的回龍塘,以扼太平軍西竄之路。 新任湖南巡撫張亮基是個能吏,他贊同江忠源的意見。但是來援諸將卻無人肯駐兵回龍塘——正是諸將都知道江忠源有見識,說的事往往都能應驗,才沒人敢去回龍塘;就怕自個兒正當太平軍之鋒,被其撕個粉碎。 1852年11月30日,夜半時分,太平軍悄悄地撤出陣地,通過浮橋到達湘水西岸。西岸駐有萬余官軍,由向榮親自指揮防堵,但他們都趴著一動不動;東岸官軍更有六萬之眾,也同樣不敢追擊。太平軍大大方方地取道回龍塘,向西北方向揚長而去。 太平軍雖解長沙圍,退出湖南,但對于湖南的影響卻并未因此立即消散。瀏陽的征義堂組織很早就假借團練名義,擴充組織,建立武裝,時間長達近二十年。在蕭朝貴進攻長沙時,征義堂領導人周國虞本打算立即起兵響應,因被官府發現而未果。當時長沙戰局吃緊,官府也顧不上料理他,只得先聽之任之。周國虞趁機發展勢力,為發動武裝起義做準備,其力量迅速擴充至兩萬多人,成為省內*大的和組織性*強的會黨武裝,并控制了瀏陽縣城及大部分縣境。 征義堂人數眾多,器械俱備,技勇頗精,非尋常會黨可比。省府不斷收到秘密報告,連遠在北京的御史也上奏,要求迅加處置。張亮基這時已將左宗棠召入幕府,左宗棠一邊采取麻痹策略,促使周國虞游移不定,不敢驟然舉起義旗;一邊密授江忠源以計,讓他以搜捕其余會黨起義軍的余黨為名,率楚勇由小路進入瀏陽,待機對征義堂進行鎮壓。 發現江忠源來到瀏陽,周國虞知道大事不好,被迫匆促舉義,并分三路對楚勇發動進攻。江忠源亦分三路進行反擊,而且很快就擊潰了征義堂,周國虞隨后也被擒殺。 瀏陽地近省城,對省城乃至全省的威脅固不待言;同時,它又位于湖北、江西、湖南三省毗鄰區,一旦太平軍卷土重來,便可里應外合,近圍長沙,遠攻江西、湖北。幾個月后,太平軍西征,表明征義堂確實是一個極大的戰略隱患;若當時不除,對清廷而言,后果不堪設想。 此役,巡撫張亮基被認為調度有方。但他只是名義上的統帥,前線指揮實際是江忠源,鎮壓征義堂的主力部隊則是江忠源所統率的楚勇。也就從這個時候起,以楚勇為代表的湖南團練武裝,開始越來越受到朝廷的倚重。 沒打算按規矩辦事 江忠源及其楚勇的成功,讓湖南地方官府及其士紳均大受鼓舞。在太平軍圍攻長沙時,湘鄉人羅澤南即受知縣朱孫詒的委托,與其門人王錱、李續賓等人在鄉辦理團練,而當時曾國藩還尚在回鄉途中。 ...... 太平軍則不然,在南王馮云山死后,由東王楊秀清掌握了統一的軍事指揮權。楊秀清轄制部隊很有一手,太平軍從進攻長沙到解圍北上,直至攻取武昌,始終能做到節制嚴明,有進無退,這在歷代起義軍中都是很突出的。與此同時,太平天國有著明確的政治理想和目標,與清朝儼然敵國;而且它在攻城略地之后即能加以鞏固,并壯大其力量。比較一下紫荊山區時代和奪取武昌時期的規模氣勢,天國實力增長之快,足以令人嘆為觀止。面對這樣前所未有的強敵,若還指望以零星團練與之作戰,簡直形同驅犬羊敵虎狼。 包括曾國藩在內,咸豐先后共在十個省份,任命了四十三人為督辦團練大臣,后來除了曾國藩,無一例外,全都失敗了。他們為什么失敗?就是都老老實實地按照朝廷所交代的去做了。 如果方向就是錯的,想不失敗都難。曾國藩走的恰恰是另外一條道路,他從一開始,就沒打算按規矩辦事。比如朝廷說,辦團的事務,你在旁邊督促指導一下就行;他不,他親力親為地去辦團。又比如朝廷說,團練只要在地方上活動,“練團查匪”即可;他也不,他說他要辦就辦“大團”,而且這個“大團”跟張亮基等地方大吏也沒太大關系,就他曾國藩一個人管! 曾國藩深信,只有建立一支既能跳出地方范圍,同時戰斗力又非綠營可比的湖南新軍,才能真正有所作為,甚而改變時局。而他所要建立的這支新軍,也就是后來人們所稱的湘軍。
亂世湘軍 作者簡介
關河五十州,: 江蘇常州人,軍事紀實文學作家。已出版《一寸河山一寸血》《戰神粟裕》《彭大將軍》《謀帥劉伯承》等多部作品。
- >
我與地壇
- >
苦雨齋序跋文-周作人自編集
- >
伊索寓言-世界文學名著典藏-全譯本
- >
詩經-先民的歌唱
- >
我從未如此眷戀人間
- >
自卑與超越
- >
有舍有得是人生
- >
李白與唐代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