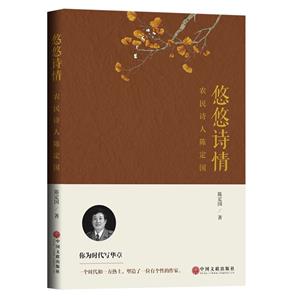-
>
魯迅全傳:苦魂三部曲-增訂版(全三冊)
-
>
大家精要- 克爾凱郭爾
-
>
尼 采
-
>
弗洛姆
-
>
大家精要- 羅素
-
>
大家精要- 錢穆
-
>
白居易:相逢何必曾相識
悠悠詩情:農民詩人陳定國 版權信息
- ISBN:9787519046729
- 條形碼:9787519046729 ; 978-7-5190-4672-9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悠悠詩情:農民詩人陳定國 本書特色
本書作者執著于傳承鄉土文化,從事業余創作已60余年,并獲得多個獎項和榮譽,他的作品里散發著濃郁的鄉土氣息,以及一直以奮斗者的姿態為詩鄉奉獻余熱的孜孜不倦之精神,可提供給廣大的創作愛好者鼓舞和啟迪
悠悠詩情:農民詩人陳定國 內容簡介
這是一部紀年體傳記,從1953年7月至2018年7月,按時間順序,以自述文逐條論述,圖、文并存,以圖為主,真實地記錄了作者在業余創作上走過的一路風景。
悠悠詩情:農民詩人陳定國 目錄
001 秀才逢生
005 我的童年
021 八形汊的故事
031 回家真好
038 四年才走上**個臺階
044 熱出一個高溫天氣
055 我在北京唱山歌
062 揚帆的詩船
078 婚事風波
095 她的愛在延續
104 詩鄉,你長大了
113 登上文化大舞臺
144 寫好人生這部書的“后記”
244 代跋 陳定國:打撈洞庭民歌
250 采訪手記 向堅守者致敬
251 后記
悠悠詩情:農民詩人陳定國 節選
秀才逢生 太陽從洞庭湖邊升起,一道道紅光灑在水面上、大堤上、楊柳上、蘆葦上,大地顯得格外燠熱。 這是 1936 年 9 月 23 日,農歷丙子年七月初七辰時,我出生于沅江白沙洲。 母親臨產的那一時刻,父親在堂屋里坐立不安,有時叭幾口旱煙,有時在屋里轉來轉去,有時心不在焉地隨手翻看那本翻爛了的《三國演義》,但心里是十五只水桶提水,七上八下。 “哇”的一聲,房里傳來一陣嬰兒的啼哭。 在我家接生的高大媽三腳兩步跨出房門,笑嘻嘻來到我父親面前,興奮地說:“恭賀先生,添個男喜!” 父親聽說生個男孩,臉上流露出無限的喜悅,丟掉手里的旱煙袋,喜沖沖地跨進房門,只見我母親躺在床上,頭偏向門外,那蒼白的臉上浮現了安詳的笑容。父親笑著說:“婆婆子,辛苦噠,辛苦噠啊!” 父親走近看了看我,虎頭虎腦的伢兒模樣,喜得就像石磨一樣地旋轉起來,從里屋轉到堂屋,情不自禁地哼起南宋詩人葉紹翁的詩句: “春色滿園關不住,一枝紅杏出墻來!” “海公先生,什么事這樣高興?” 父親抬頭一看,正是方恕庵先生。 方恕庵又名方槦,清朝光緒末期拔貢,很有名望,白沙洲的**個文人,善詩詞,愛書法,有“方秀才”之稱。 父親也精通文理,喜歡舞文弄墨。兩人常在一起吟詩作賦,談今論古,講得*多的是《三國演義》《西游記》。他們還悄悄聽過縣里的地下黨員的講演,心情開朗起來,常和窮朋友在一起講紅色故事,傳紅色歌謠。窮朋友說他們是開明人士,他們說窮朋友是知心朋友。 今天,父親洋洋得意,當著方秀才的面隨口而出: “看今日喜添貴子。” “恭喜,恭喜。”方秀才忙忙拱手道喜,高興地對下句: “望未來光耀華堂。” 二人哈哈大笑。 “小少爺的大號是……”方秀才問。 “你來得正好,請取個名字。”父親十分尊重他。 “好,我想想。”他在堂屋里坐下來,接過張大媽端上來的熱茶,慢條斯理地品起來。 這時,我突然在房里幾聲啼哭,連小湖那邊都能聽見,驚飛了門外大樹上的喜鵲。 “好家伙,有底氣!”方秀才不覺喃喃自語,“孩兒今后必有出息,我看,就叫定國吧。” 父親連連點頭:“好,好。” 父親摸出一壺米酒,一碟子炒豌豆,與方秀才對酒暢談。談著談著,談起了自己的即興創作。 父親抿口米酒,興致勃勃地吟了起來: 洞庭月色醉藍天, 報曉金雞啼在先。 氣概昂揚天下白, 安邦定國夢圓圓。 方秀才也抿一口米酒,應和起來: 定有蛟龍雪浪游, 國中喜氣遍河洲。 苗苗迎著春風長, 喜望曙光照彩樓。 他們二人都是將我的名字“定國”嵌入詩中,只是方秀才的更加高明,吟的是藏頭詩。父親連忙打拱手,斟上滿滿一杯酒,敬給方秀才,說道:“方兄,佩服,佩服。” “干!”方秀才一飲而盡。 這時,高大媽走了出來,與我父親講了幾句耳語,父親連忙把方秀才請到里屋。 “看看細伢子,看看。”高大媽用紅格子被單緊緊包著我,抱起來,站到父親和方秀才面前。 我父親滿臉笑容,非常得意地在我那粉嘟嘟的臉上輕輕吻一下。他那胡渣像鋸齒一樣,刺得我哭了。 方秀才趕忙在我身上輕輕地拍了兩下,笑著說:“啊,好孩子,別哭,別哭。” 我真的不哭了。 高大媽把我抱到母親懷里。母親笑著向方秀才輕輕揮手:“請坐請坐,秀才進屋,全家得富。” 高大媽喜得拿一根穿了紅線的縫衣針,別到方秀才的左臂衣袖上。 方秀才曉得,誰家生了小孩,**個進門的外人就是“逢生”,男的稱“逢生爹”,女的稱“逢生娘”,年輕人就稱“逢生哥哥”或者“逢生姐姐”。不管是誰逢生,主人必須在逢生人的衣袖上穿紅線針。這是湖鄉人的風俗習慣,表示對逢生人的一種喜愛與尊重,而逢生人則得到喜悅與榮耀。 接著,高大媽又給方秀才送來一碗糖水雞蛋茶。方秀才接過碗,輕輕地抿了一口糖水。 方秀才臨走時,慢慢地取下紅線針,放在《三國演義》這本書上。按傳統風俗,紅線針應插在門前樹上,暗示小孩四季常青,長命百歲。而他把紅線針放在書上,自語:“腹有詩書氣自華!” 父親聽了,笑得合不攏嘴。 那時,我家是掰著手指過日子,很窮。方秀才家里好得吹油不開,很富有,常常周濟我家一些錢米。在我“三朝”那天,他以逢生爹的身份,特意送來厚禮:白米六斗、豬肉六斤、黑雞六只、紅棗六斤、黃花六斤、雞蛋六十雙,銀圓六十塊。還用紅臘光紙寫了一副對聯,那就是我出生那天他和我父親的即興創作: 看今日喜添貴子; 望未來光耀華堂。 我的童年 難忘我的童年,**個小鏡頭:躲日本 1943 年 3 月,我快七歲了。 值插秧時節,沅江來了日本鬼子,父老鄉親嚇得要命,拖兒帶女往外逃。我母親一手拉著我的手,一手提一藍布袋子衣服,我父親背上挎床用繩索捆緊的白土布棉被,也外出逃難。好像日本鬼子從后面追來了,沒有目的地舍命往前跑,到了桃江鸕鶿渡、安化馬跡塘,寄居在山里人家。我母親藏在衣角里的一塊銀圓也用完了,只得逼著往回走,走到沅江臺公塘的一個親戚家里住下來,白天躲在竹山里。 這一天,有人從南縣廠窖那邊來,說起了日本鬼子血洗廠窖的事。那天天氣由晴轉陰,非常悶熱,后來慢慢地刮起了西北風,人們才喘了一口氣。路上走來一位挑擔秧夾子的年輕大漢子,突然望見一里路外的大堤上開來—路長長的隊伍。隊伍走近了,他就看見一面太陽膏藥旗。他急忙甩下秧夾子,掉頭回跑,雙手亂舞,大聲喊:“日本鬼子來了 ! 日本鬼子來了 !” 頃刻,好似洪水沖垮了大堤,人們喊的喊、哭的哭、躲的躲、跑的跑,一下子整個村子人心惶惶。那位年輕大漢拉著年邁的父親,肩背兩皮木槳,**個跑到河邊,劃船逃命。不一陣子,成群集隊的村民也趕到河邊,上了大小不同的船只,都想躲到對岸的蘆葦蕩里去。哪知一艘日軍汽艇迎面而來,“叭叭叭”,一陣密如雨點的子彈朝船掃射,木劃子打得嘣嘣響,水上擊起點點浪花。船上的村民無處藏身,只能往艙里爬,往河里跳。汽船逼近,槍聲更緊,殺得血水成河,尸沉水底。那位年輕大漢的父親中彈身亡,他含淚從船邊跳到河里,順手撈塊浮在水面的船板,掩蓋頭部,潛水爬上岸來,伏在河灘上一個長滿了野草的土凼里,才逃過一劫。大堤邊那些拖兒帶崽、痛哭流淚的村民在舍命奔跑,一個嫂子踉踉蹌蹌跪倒在地,膝蓋流血,她看也不看一眼,摸也不摸一下,爬起來又跑。大家跑著跑著,遇上躲在一邊的幾個鬼子,一陣機槍橫掃,頓時血染河堤,尸首滿地。這時,“嗡嗡嗡”一陣響聲,兩架日本飛機飛過來,低空盤旋,扔下顆顆炸彈。村里濃煙滾滾,一間間民房大火沖天,一處處尸首堆積如柴…… 我雖然沒有親身經歷這事,但日本鬼子的惡行在我的心里留下了陰影。我并沒有看到過日本鬼子,但聽到許多關于他們燒殺擄搶的事,還有我家在驚恐中度日的經歷,深深記在我的心里。 誰不痛恨日本鬼子,只愿那班強盜早些發瘟。我父親想了一副抗日楹聯: 雙拳推動海島; 一腳踏平西山。 我不懂海島、西山是什么意思,父親告訴我,都是指日本鬼子。 我們全家躲兵回來不久,方秀才病故了。 聽說他在臨終前囑咐家里人三件事:一是葬禮從簡、薄葬;二是家里的全部資產給張家塞的窮人(他的岳父家在益陽縣張家塞);三是所有田土無償佃給白沙洲的窮人。他僅留給后人的是他生前寫的四十一本日記和四大冊詩詞歌賦。 這天,云霧迷茫。我跟隨父親母親到了方秀才墳地,肅立在瑟瑟的秋風里,心隨著被湖風掠過的柳條而抖動。母親望著那三尺高的細石墓碑,放了一掛千子鞭,燒了一疊錢紙。父親站在墓碑前,深深鞠一躬,嘶啞著嗓子念著悼念方秀才的挽聯: 落筆生輝傳天下;為民獻業貫古今。 我拱手作揖,彎腰鞠躬。心里念著:逢生爹爹,你不能再來看我了啊! 第二個小鏡頭:讀私塾 我長到八歲,在大伯家讀私塾。 大伯叫陳德福,是白沙洲有名的開明老教書先生,面相富態,一臉笑容,穿件青布長袍子,戴副老花眼鏡。學堂設在大伯家里堂屋,課桌凳子都是學生從自己家里搬來的。 每天上午九點上學,下午四點放學,啟蒙的**本書是《三字經》。每上一節課先由先生教,后是學生讀,再是先生點,學生背。每次大伯點書后,滿屋八九個學生,作鼓正經地坐在位子上一聲一聲地讀,唯有我不聲不響地看。 “你何解不讀?”大伯走到桌邊問我。 我冒冒失失地反問大伯:“你老人家何解見我沒讀?” “你明明沒開口讀書呀。”大伯不高興,翻臉比翻書還快。 “我在心里讀咧。” “好,我來點書考考你。” “你老人家不要點。” “先生不點書,那是一只豬。”大伯生氣了。 “大伯,你點的書我背得。” 大伯馬上點書,他點上句,我背下句;他點一段,我背一段;他點一頁,我背一頁。每字、每句、每段、每頁背得“一溜之煙”。我由此深得大伯喜愛,他說:“定國,看不出,看不出,你不要我勞神哩。” 一天中午,我大伯外出喝喜酒,就吩咐我帶著同學讀書,并向同學們宣布由我點書。 我有模有樣地點書,大家都背得。我一看時間還早,就雷急火急地帶立伢子和幾個同學,翻過大堤,在堤外河灘的楊樹上掰枯丫枝,只有一餐飯久,每人掰一捆,背到大伯的灶屋里,碼起了一大堆。 大伯回來了,灌得臉紅紅的,額頭上暴起一條條青筋,像蚯蚓一樣。他見到灶屋里的柴禾很生氣,繃著臉,瞪著眼,醉言醉語地沖著我問:“誰要你們去掰樹上的枯丫枝?” 我毫不隱瞞地說:“是我要他們去的。” “這是闖禍!” “不是闖禍,掰掉枯丫枝,是為樹整枝,讓樹更好地發育成長。” “何解把樹丫枝搬到我屋里來?真淘氣!” “你天天為同學們熱中飯、燒茶,這不要用柴呀?我們是為自己撿柴哩。” “講得頭頭是道!這明明是為我撿柴吶。” 大伯想起昨天在課堂上的那個考題:家里養的魚被貓吃了,這怪誰?同學們都說怪貓,我有不同看法,貓是愛吃魚的,主人應該做好防備。 想到這里,大伯鄭重宣布:“今朝我沒防備你們去撿柴,教不嚴,師之惰,我有責任。” “我的責任。你外出了,我就是主人。” “定國,你不要講了,貪財是萬惡之根”,大伯理直氣壯地說,“先處罰我。減少每人一毛錢學費,等于向你們買了這些燒柴。” 我說:“不行,先生要罰學生才是。” “當然要罰你們的。”大伯推推鼻梁上的眼鏡,接著提出,“罰你們對對子。誰要是對不上,用竹板打屁股。” “莫打同學們,要打就打我!” “定國,你真是好漢做事好漢當。那我先‘罰’你,你聽題: “春風。” “細雨。” “春天。” “夏季。” “正氣。” “春光。” “萬里。” “千年。” “日照。” “風傳。” “書聲。” “妙語。” “爬雪山。” “撒火種。” “枝枝綠竹生新筍——” “……”我卡住了。 “你怎么對不上了?” “大伯,我還沒學七字對。” “二字、四字、七字、十字,更多的字都是按詞按字按聲韻平仄相對的對法。” “好,請大伯再念題。” “枝枝綠竹生新筍。枝枝對什么?綠竹又對什么?” 我真是——和尚失了臘肉,開不得口。 大伯見我答不出來,就動手拿起竹板,在我眼前一閃一閃的。 “我來對。”立伢子插話,“捆捆……” “不要你插嘴!”大伯用竹板指著他,又用竹板指著我,“你對不上呀。”大伯見我是**次對長對子,就啟發我:“你看看菜園里。” 我抬頭看見菜園里那棵梅樹,計上心來,我腦子靈活,來得快,想了一想答道:“朵朵紅梅報早春。” 大伯的目光盯著我,點頭微笑,但他故意問那幾個沒去撿柴的同學:“該不該打他的屁股?” 滿堂同學從座位上站起來回答:“他的對子對得好,不該打他!” 我愛讀書。每天從私塾回家,除了在家里勞動和幫三伯看牛外就是看書。有天下午放牛,我坐在堤邊草地上,捧起一本書看起來,一下子入迷了,忘記看住牛,結果牛跑到李家媽的菜土里吃掉六蔸大白菜。我趕快把牛趕回草坪,打算回家后,再去向李家媽賠禮。哪曉得,李家媽到園里摘菜,發現了牛腳印,生氣地喊:“這是哪個看牛伢子不看好牛啦。” 我闖的禍,不能瞞她,也不能推在別人身上,連忙走上去認錯,把衣袋里僅有的一分錢拿出來,補償損失。她橫豎不肯要,撲哧一下笑了:“沒事,沒事,你是在讀書呀,幾蔸白菜算么子呢?” 立伢子從那邊青草坪看牛趕過來了,約我明天放學后,在青草坪看牛對山歌。
- >
煙與鏡
- >
山海經
- >
朝聞道
- >
羅曼·羅蘭讀書隨筆-精裝
- >
巴金-再思錄
- >
名家帶你讀魯迅:故事新編
- >
自卑與超越
- >
我從未如此眷戀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