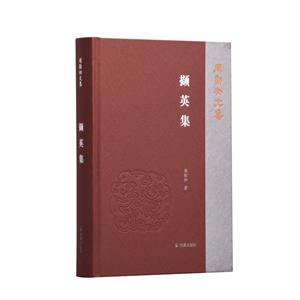-
>
百年孤獨(2025版)
-
>
易中天“品讀中國”系列(珍藏版全四冊)
-
>
心歸何處
-
>
(精裝)羅馬三巨頭
-
>
野菊花
-
>
梁啟超家書
-
>
我的父親母親:民國大家筆下的父母
擷英集(周勛初文集) 版權信息
- ISBN:9787550634305
- 條形碼:9787550634305 ; 978-7-5506-3430-5
- 裝幀:一般純質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擷英集(周勛初文集) 內容簡介
《擷英集》是原江蘇社科名家文庫中的一卷。該書是文史學家周勛初先生傳記,他的學術研究涵蓋中國古代文學史、中國文學批評史、中國古典文獻學和中國古代思想史諸多領 域,研究時限上起先秦下迄近代,體現了文史結合、博通與專精結合、宏大與細致結合的治學特點。本書分為三大塊:1. 學術小傳:我與傳統的文史之學。在進入高等學府深造、 不斷推出研究成果、力求在學術上有所創辟、部分成果綜述、教書育人和對外文化交流等幾方面敘述中,展開作者一生學術生涯的總結。2.代表性學術成果。分列六個專欄,文史研究、序、敘錄、訪談錄、前言后記、教學講演,分別介紹了有影響力的學術文章25篇。3.學術年譜。
擷英集(周勛初文集) 目錄
目錄
學術小傳——我與傳統的文史之學
一艱難困苦,終于進入高等學府深造
二見縫插針,不斷推出研究成果
三獨立思考,力求在學術上有所創辟
四部分成果綜述
五教書育人
六對外文化交流,傳播中華文化
代表性學術成果
**篇文史研究
東皇太一考
戰國時期的幾起變亂佚史
秦漢宗教一般
魏氏“三世立賤”的分析
“登高能賦”說的演變和劉勰創作論的形成
“折衷”=儒家譜系≠大乘空宗中道觀
——讀《文心雕龍·序志》篇札記
梁代文論三派述要
李白兩次就婚相府所鑄成的家庭悲劇
柳珵《劉幽求傳》鉤沉
唐代筆記小說的校讎問題
從“唐人七律**”之爭看文學觀念的演變
敘《全唐詩》成書經過
文學“一代有一代之所勝”說的重要歷史意義
第二篇序
武秀成《〈舊唐書〉辨證》序
王華寶《古文獻問學叢稿》序
第三篇敘錄
《隋唐嘉話》敘錄
《次柳氏舊聞》敘錄
第四篇訪談錄
就《唐語林校證》事答客問
第五篇前言后記
《韓非子校注》導讀
《唐鈔〈文選集注〉匯存》前言
《唐語林校證》前言
《宋人軼事匯編》前言
《當代學術研究思辨》增訂本后記
第六篇教學講演
新材料的利用和舊學風的揚棄
——讀王國維《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
選龍二學百年沉浮
——從教學工作之一角看世運變遷
學術年表
擷英集(周勛初文集) 節選
—擷英集 學術小傳— 一艱難困苦,終于進入高等學府深造 我于公元1929年生于上海郊區南匯縣西周家宅的一個中小地主家庭。中、小學階段,由國民黨統治到淪陷于日本侵略者,抗戰勝利后又恢復到國民黨統治,兵荒馬亂,生活極不穩定,學習極不正常。小學讀了五年,換了四個學校,中間還從一位秀才讀了半年私塾。高小五年級未讀,跳級進入上海靜園小學,突擊記下英語二十六個字母,隨后慢慢補課直到畢業。父親周廷槐先生,畢業于光華大學中文系,曾在全校作文比賽中奪魁,得到校長張壽鏞的賞識,留在本校當職員,兼任附中教師,但在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后即告失業。我也在讀了一年初中后失學回家。閑居一兩年后,又跳級就讀附近鎮上的周浦中學,畢業之時正值日寇投降,父親找到了工作,我又有了機會進入上海滬新中學讀書。父親深感文科學生求職困難,于是讓我就讀理科。該校只上半天課,化學、物理負擔很重,但從未做過一次實驗,紙上談兵,學的都是空頭理論。況且初中時未讀小代數,高中二年級上大代數,一直處在似懂非懂的狀態,僅能勉強應付。后來我才懂得,我的學習歷程違反了循序漸進的原則,既學不好,還感到吃力。 高中三年級時,我突然大口吐血,始知患了嚴重的肺病,不得不回家修養。當時醫藥界采用靜臥療法,三年床褥,瀕死者再,只是依仗父母的慈愛、兄妹的護侍,才能茍延一息。第二年時病情惡化,幸虧鏈霉素進入上海,才免于一死。但家庭經濟日益陷于困境,只能不斷變賣家產度日。 全國解放,家庭發生巨大變化,我遂勉力以同等學力考入南京大學中文系。以前學的數理化全已遺忘,不得不考文科。只是入學不到半年,發現肺病仍未痊愈,不知高考體檢時因疏忽而讓我漏網了呢,還是其時適值有所好轉,這時又告復發?萬般無奈,只能轉入療養宿舍,直到三年級結束時才恢復健康,轉入正常的學習生活。 國家新建,需要大量補充新干部,于是我們1950年入學的一屆讀了三年之后提前畢業,分配工作。這時我剛結束長達七年的肺病生涯,怕不能驟然投入繁劇的工作,而且覺得因病耽誤了學習,也想補讀一些書,于是我向系主任方光燾先生表白了這一想法。方先生向來愛護學生,他沉思了一番,說:“下一學期胡小石先生要開文學史課,他已是六七十歲的人了,以后不可能再開這課。機會難得,你也不要再聽其他什么課了,這一年你還是集中聽胡先生的課,跟他學吧。”胡先生聽到我要跟他再學一年,也很高興。但開學**天,慕名而來聽課者甚多,主管人事的一位干部就來阻攔我入內,說是以前已學過不能再聽。我據理力爭,仍未如愿,不得已,只能轉向方先生求助。方先生赫然震怒,由于他的干預,我才有機會再次跟胡先生學習。事后方先生還說,應該把我留下當助教,只是礙于他正當政,不便提出。總的說來,大學四年,只有這一年才利用這次難得的機會用功讀了些書,奠定了我日后研究工作的基礎。 大學畢業,胡小石、羅根澤兩位老師向校領導推薦,希望把我留下任教,但終因出身不好、表現不合領導要求而不能留校。對此我并不怪怨任何人,根據當時的標準,我自然不能進入本校教師行列。 這時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新建,需要人,國內已無當屆大學生供應,因此才有機會進入該會的漢字整理部。前后兩年半工夫,主要做編制發布《漢字簡化方案》的具體工作。1956年時,知識分子政策出臺,胡小石先生開始招收副博士研究生,他希望我回去繼續跟他學習,于是在年底又考了回去。 自此之后,我再也沒有離開過南京大學。1959年改為助教,1961年升為講師,1980年升為副教授,1984年國家教委特批為教授,1986年被批準為博士生導師。直到1984年,我從未出任過任何行政職務,連小組長都沒有當過,自此時起,才先后出任南京大學古典文獻研究所所長、南京大學研究生院副院長,隨后又在國家文教機關和省內的一些機構內擔任了職務。 在政治標準**的時代,我自然甘居人后,而在計劃經濟的形勢下,自然服從組織安排工作。我的經歷也就決定了我的身份,即政治條件很差,不能承擔重要職務,但做事也還認真,因而可以干一些具體工作。政治條件寬松時,我總能作出一些成績。1956年時,就因制訂發布《漢字簡化方案》工作成績突出而當選為國務院直屬機關青年社會主義建設積極分子。其后極左思潮開始抬頭,處境也就日益艱險而永無受表揚的機會了。平時只能不斷地做些具體工作。建國初的十七年,運動不停,突擊不斷,諸如大編教材,修訂《辭海》,搞法家著作,等等,都得參加。教過的課中,中國文學批評史先后講過兩遍和兩個學期的上半段,這已算是我教學時間*長的一門課了。任務不斷改變,學習上缺少長期打算,不可能系統地積累某一方面的資料。因此我對學習情況的自我鑒定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調,隨波逐浪,力疲心勞。 可以說,直到80年代前期,我一直處在打雜的位置上,始終不知道自己有什么專業。由于我對家庭的那份感情、對師長的親密關系,因而“地主階級孝子賢孫”、“封建學者俘虜”等帽子一直懸在頭上,“文化大革命”中終于公開蒙此惡名,為此發送農場勞動時也得加倍延長時間。只是天網恢恢,密而有漏,外恃若干領導的善意對待,內恃妻子的理解和支持,終于挨過政治上的重重高壓,步入改革開放的新時期。 二見縫插針,不斷推出研究成果 我也有一些優點,做事還算認真,讀書還算勤奮,而且自知條件不如別人,不能指望上級給你什么優惠條件,因此承擔某一任務時,如有心得,總想及時記錄下來,以免轉向后遺忘。我早期所寫的幾本書,都是在任務改變前夕突擊出來的。 大學階段,跟胡小石師學《楚辭》,收獲*大。研究生時,小石師本想讓我作《山海經》的研究,后因急于接替重病在身的羅根澤師上中國文學批評史課,這才趕忙把學習《楚辭》時考慮過的一些問題寫下,因為時間限制,只能就其中《九歌》方面的問題略抒己見,也就寫成了后來正式出版時取名為《九歌新考》的**本書。 改助教后,為五年級上中國文學批評史課。我在研究生階段只上了一年多的甲骨、金文和《說文解字》部首,這時轉向立即上高年級的新課,從孔夫子到王國維,全由我一人承擔,吃力得很。但我集中精力備課,第三年時就發表了《梁代文論三派述要》一文。“文革”前夕,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約我寫作“中國古典文學基本知識叢書”中的《中國文學批評簡史》一書。書稿完成后無法交出,直到80年代初期,經改寫后才以《中國文學批評小史》一名問世。 “文革”十年,荒廢年華,但由于我的特殊身份,即沒有任何價值,卻還有那么一點使用價值,故而后期被起用。先是參加江蘇五所高校集體編寫《馬恩列斯文藝論著選讀》的注釋工作,同時參加《辭海》的修訂,后又參加我校和南京化學工業公司師傅組成的法家著作《韓非子》注釋組,還利用空隙時間寫成了《韓非子札記》一書。“文革”結束,我又受命將注釋稿改寫成一本學術著作,增加校勘等方面的內容,以《韓非子校注》一名正式出版。 此前我曾奉命將家中“黑書”悉數上交,因而除了“雄文四卷”之外已無書可讀,后因出現了郭沫若的《李白與杜甫》一書,工宣隊開禁,允許教師讀讀唐詩。精力無處發泄,潛心閱讀,隨后寫成《高適年譜》一書。“文革”結束,有事上北京查書。一個偶然的機會,得知故宮博物院圖書館中藏有胡震亨《唐音統簽》和季振宜《全唐詩》二書,經請求蒙允準,花了半個多月精心閱讀,隨后寫成《敘〈全唐詩〉成書經過》一文,由此進入了唐詩研究的行列。1990年時,我主持了一次唐代文學國際會議,為了總結唐詩研究各方面的成就,我主編了一本《唐詩大辭典》,并寫了《唐詩文獻綜述》一文作為附錄。其后又為李白的一些奇特現象所吸引,試圖作出新的解釋,從而寫下了《詩仙李白之謎》一書。也就在同一時期,我奉校方之命,協助匡亞明前校長主編《中國思想家評傳叢書》,匡校長要求每位副主編都寫上一本,于是我于本世紀初完成了《李白評傳》一書。 1980年前后,我應中華書局友人之約,整理筆記小說《唐語林》。其成果即《唐語林校證》上、下兩冊。隨后我就整理過程中發現的一些問題繼續探討,寫成《唐人筆記小說考索》一書。與此同時,我主編了一本《唐人軼事匯編》,由我所內人員嚴杰、武秀成、姚松負責具體編纂。出版之后,頗獲時譽,于是我在90年代后期又籌劃重編《宋人軼事匯編》一書,具體工作由校外專家葛渭君、周子來、王華寶三人負責。此書已于2014年完成出版。 80年代,我花在唐代文學方面的精力較多,因此比較關注陳寅恪、岑仲勉等人的研究成果。其后接受程千帆先生的建議,為碩士生開設近代學者治學方法研究一課。到了90年代,我將這一方面的論文和講義編成《當代學術研究思辨》一書,公開出版。 除了寫書之外,我還先后寫過一百幾十篇論文,先是編了《文史探微》、《文史知新》、《魏晉南北朝文學論叢》三本論文集。所收文章,上起先秦,下至當代。文章內容,以文學為主,但又不囿于純文學的范圍,而與傳統意義上的文史之學聯系密切。這與我的師承有關,也與我個人的特殊境地有關。 除此之外,我還先后編了兩本論文集——《無為集》與《馀波集》,把那些零散的文字又匯集起來,前者編入了《周勛初文集》,后者則于八十壽辰時編就出版。 全國高校古委會成立,我出任本校古籍所所長,于是又把很多精力投入古籍整理項目。其中規模較大者,一是與一些友人主持《全唐五代詩》的編纂,出任**主編,希望總結唐詩文獻整理方面的新成果,編成一本質量上超過清代康熙御定《全唐詩》的嶄新總集。一是組織我古籍所與中文系古代文學教研組內同人,整理出一部《冊府元龜》的校訂本。這本書猶如一座未被開發的寶庫。我們將宋本與明本互校,并與史書互核,后且附以人名索引。這就為文史學界的研究工作者提供了不少便利,出版后得到很高評價。 90年代,我還做了一件頗為愜意的事,將我國流散在外的珍貴古籍唐鈔《文選集注》迎歸故土,編輯加工出版。此書以日本《京都帝國大學文學部影印舊鈔本叢書》內的二十三卷殘帙為基礎,加入臺灣“中央圖書館”所藏的一卷,天津藝術博物館藏的一卷殘帙,北京圖書館所藏的兩片殘頁,按一百二十卷本原來的順序編排,命名為《唐鈔文選集注匯存》。本世紀初,我又籌劃出了一種增補本。各界朋友共襄盛舉,我能為此稍盡綿薄,實屬三生有幸。 三獨立思考,力求在學術上有所創辟 我是干一行,學一行,隨之寫下一些東西,留作人生記錄。 我在大學本科和副博士研究生階段,集中精力學習過《楚辭》。由于師承的緣故,我的治學道路有違時尚。1953年時,世界和平理事會定屈原為世界文化名人,學術界掀起過一陣屈原熱。當時發表的文章大都以“人民詩人屈原”、“愛國詩人屈原”為題,著重論證他愛祖國愛人民的一面。關于《離騷》等作品,則從積極浪漫主義寫作方法等角度予以褒揚。我對這種研究方法不感興趣,喜歡從神話學、宗教學、民俗學等方面進行探討。當時這類書很少,圖書館中已把建國之前那些談神說鬼之作束之高閣,境外新書又不能入內,但一次偶然的機緣,我從古籍書店中忽然看到一本香港饒宗頤先生的《楚辭書錄》。此書后附論文索引,很多是發表在民國時期舊雜志上的論文。剛巧那時我新婚,妻子祁杰還在北京工作,假期中我都要去探親,于是按照索引上的提示,到北京圖書館期刊室中借閱。在當時來說,我的閱讀面要比別人廣,上至王逸、朱熹等人的著作,下至蘇雪林、何天行等人的論文,都曾鉆研。這一時期的人強調觀點,舊雜志上的文章,一般人已棄之如敝屣,而我卻努力探討他們提出的新見是否可以成立,與當時年輕人應該走的方向是不合拍的。 寫作《九歌新考》時,我的操作過程比較規范,先是廣泛占有材料,然后歸納成幾種學說,分析他們的得失,然后提出自己的看法。“《九歌》異說綜述”一章中,把古今有關解說《九歌》性質的學說分為“忠君愛國”、“民間祭歌”、“楚郊祀歌”、“漢人寫作”四種學說,隨后以《屈原創作說申述》為總結。這一結論,是在考察了先秦兩漢神話、宗教、民俗的前提下,對《九歌》諸神一一進行分析研究,并與各家展開討論,否決了以上四說的基礎上提出的,這里有我的新見。 這是我**部完成的專著,留下了學生時代的痕跡,許多重要論點,發揮師說而成。小石師曾指出,東皇太一可能是齊國的神,楚人不能祭祀河伯,這都成了書中的重要章節。小石師學問博大,讀書神悟,但他秉承前代學風,不輕易動筆,只在講課時提出某種觀點,而不作詳細論證。我在學習《楚辭》時曾對各家之說一一比較,*后確信小石師的看法*有道理,從而服膺師說,并在他的提示下深入研究,證成此說。由此我就想到,師生之間的學術傳承猶如接力賽跑一樣。教師提出某種觀點,學生得到啟發,從而在這一點上進行開拓。從學術的發展來看,每一種學說都是在繼承的基礎上進行的。 小石師是清道人的學生,接觸過清末的不少學者,他繼承樸學傳統,而又采擇西洋新興學術。我在他的指導下,也曾學過一些小學方面的著作,并對文史不分的傳統表示認同。 所謂“文史不分”,從目下的情況來說,當然不能僅指文學、歷史兩門學科。我國古時所說的“文史”也不是這個意思。“文史”的內容是很廣泛的,它包括了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的許多門類。哲學、宗教,等等,尤與歷代文人的思想有關,研究文學,自不能不對此有所了解。 因此,我主張綜合研究,為此我曾一再申述。《文史探微》的“后記”中說,我在學習文學作品時,往往連類而及,也相應地讀一些史書或哲學著作,這樣做,是希望對古代學術能有更完整的認識。因為在歷史上,無論是一種風尚、一個流派、一部著作的形成、發展和變化,都是紛糅交錯地呈現出來的,后人當然可以分別從文、史、哲等不同角度進行探討,但若能作綜合的研究,也就可以理解得更全面,更深入。這里我還可以補充一點,就是擴大知識面后,在探討問題時往往可以取得觸類旁通的良好效應。 古代文士大都信從“一物不知,儒者之恥”的古訓,因此關注的事很多,寫作的范圍極其廣泛。后人自可從事純文學的研究,把他們的詩歌和部分散文從整個創作內容中分離出來,但這樣做常是只見樹木不見森林,難得把握整體。因此我們從事古代文學的研究,困難之一就在于合適地處理專與博的關系。從我本人來說,盡管個人資質駑鈍,還是希望盡可能地多懂得一些。1995年我主持了一次魏晉南北朝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提交的論文是《魏晉南北朝時科技發展對文學的影響》。因為我注意到,其時文人大量寫作《刻漏銘》、《相風賦》之類的作品,又喜用“玉輅勝于椎輪”之類的比喻,說明文學的今勝于古,這不是說明其時自然科學方面的進步推動了文學思想的發展么?每一個作家處在各種社會思潮的交叉影響之中,如果我們局限一隅地進行考察,怕難以掌握全貌。 如上所云,我因任務急需,做過各種各樣的工作,諸如校勘、注釋、翻譯、匯編、輯佚、考訂、闡發,等等,古代文學研究中的各種行當,大都嘗試過。不過這樣長期打雜似乎也有一些好處,觀察問題和處理問題的適應性有所增強。發現問題后,隨之就會想到用哪一種方法去處理*為合適,回旋的余地也就大些。例如我在整理《唐語林》時,發現內中一則劉幽求故事,當是柳珵《劉幽求傳》的佚文,頗欲撰文介紹,但一時又難決定用何種方式表達為佳。后來我寫了《柳珵〈劉幽求傳〉鉤沉》一文,共分三段,首先作資料介紹,中間作文字注釋,*后作理論闡發,這或許也可說是多層次、多角度地進行研究吧。目下學界中人往往從事單項研究,或擅長注釋,或擅長賞析,或擅長考證,或擅長發揮,或擅長搜集資料,猶如某一專業戶,如遇不合自己脾胃的材料,往往視而不見。一個人若是具有多方面的興趣,并有相應的駕馭能力,則可充分利用所得材料,制作成各種合適的成品。我在唐代筆記小說研究方面所以能不斷開拓,當以接受的訓練比較多樣有關。
擷英集(周勛初文集) 作者簡介
周勛初,上海南匯人,1929年生。1954年畢業于南京大學中文系,分配到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工作,1956年底考回母校讀副博士研究生,未及畢業即留校任教,自此后一 直任教于南京大學。周先生治學涉及諸子學、中國古代文學、中國文學理論與批評、中國古典文獻學、近現代學術史等學科領域。現任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江蘇省文史研究館館長, 中國唐代學會顧問,中國古代文學理論學會顧問,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顧問。
- >
李白與唐代文化
- >
史學評論
- >
二體千字文
- >
我從未如此眷戀人間
- >
中國人在烏蘇里邊疆區:歷史與人類學概述
- >
我與地壇
- >
推拿
- >
伊索寓言-世界文學名著典藏-全譯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