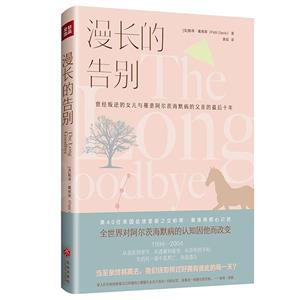-
>
魯迅全傳:苦魂三部曲-增訂版(全三冊)
-
>
大家精要- 克爾凱郭爾
-
>
尼 采
-
>
弗洛姆
-
>
大家精要- 羅素
-
>
大家精要- 錢穆
-
>
白居易:相逢何必曾相識
漫長的告別 本書特色
1.美國第40任總統里根*小的女兒帕蒂·戴維斯傾心記述罹患阿爾茨海默病的父親的*后十年 帕蒂·戴維斯,里根*小的女兒,曾因政見不同與家人決裂,以叛逆的行徑震驚世人。因父親患上阿爾茨海默病,她與父親和解,重回家庭,與家人共同開啟了一段漫長的告別旅程,并以日記的形式記錄了陪伴父親的日子,以及童年記憶里與父親、與家人的彌足珍貴的共處時光。 2. 關注全人類共同面對的醫學難題,直面每個成年人不可避免的心理挑戰 平均每3秒鐘全球就會產生一位阿爾茨海默病患者,我國目前有1000多萬患病人群,關心和照護阿爾茨海默病群體,已成為全人類共同的課題。 面對父母至親終將老去的現實,我們該如何珍惜與之相伴的每一天?當那一天終將到來時,我們該如何與他們好好告別,又該以怎樣的態度繼續以后的生活? 3. 內容與形態雙重匠心打磨,絕版十年后的再造與升級 特邀擅長文學翻譯的譯者精心重譯,親人間的溫情與細膩柔軟的力量氤氳紙上。文本經譯者與編者數次推敲打磨,力求還原原著之精髓。 形態與內容珠聯璧合,書名字體仿阿爾茨海默病做“漸退”設計,封面上的馬、橡樹、風箏等象征著作者記憶中與父親一起度過的珍貴時光。 4. 全世界對阿爾茨海默病的認知因里根總統而改變 過去人們對阿爾茨海默病毫無概念,這種狀況因里根而發生了改變。里根被確診患上阿爾茨海默病后,就向社會公開了自己的病情,以自己的知名度喚醒全世界對這種病的關注,并在1995年成立了里根和南茜研究所,專門研究這種疾病。
漫長的告別 內容簡介
本書是一部感人至深的回憶錄, 作者以日記的形式, 回憶了她與父親從前的美好時光, 搜索了所有對父親的記憶, 再一次觸摸他, 聆聽他的聲音, 栩栩如生地重現了父親的可親可敬, 字里行間流露出女兒對父親*真摯的愛與不舍。作者筆鋒簡潔流暢, 坦城感人, 字里行間中展現出了內心的熾熱情感和夾雜著震驚、無助的心緒的錯綜復雜的百味人生。
漫長的告別 目錄
1995 年4 月 / 希望的光芒
1995 年5 月,洛杉磯 / 死亡:生命永恒的伴侶
1995 年6 月 / 一次重生之旅
1995 年6 月末 / 面紗
1995 年7 月 / “漫長的告別”
1995 年7 月末 / 偉大的愛情
1995 年8 月,洛杉磯 / 父愛如山
1995 年8 月 / 失落、恐懼、成熟
1995 年9 月 / “只要我還能說話”
1995 年10 月 / 充滿情感的心臟
1995 年10 月末 / 定格在心中的畫面
1995 年11 月 / “我已經八十四歲了”
1995 年11 月,洛杉磯 / 平靜之下的巨大力量
1995 年12 月 / 夢境
1995 年圣誕假期,洛杉磯 / 河流與牧場
1996 年1 月 / 陰沉的世界
1996 年2 月,洛杉磯 / 苦澀的甜蜜
1996 年3 月 / 你將如何度過*后的日子
1996 年4 月 / 愛的紐帶
1996 年4 月,洛杉磯 / 牧場里,他無處不在
1996 年5 月 / 里根圖書館
1996 年7 月,洛杉磯 / “就像在和云彩說話”
1996 年7 月 / 刻在照片中的記憶
1996 年8 月 / 失去牧場,父親缺席
1996 年10 月 / 他正在慢慢離去
1997 年2 月,洛杉磯 / 活在當下
2004 年6 月3 日 / 月圓之夜
2004 年6 月4 日 / 那一刻已經近了
2004 年6 月5 日 / 他從未離開
后記
漫長的告別 節選
1995 年7 月 “漫長的告別” 與所愛之人道別, 那句再見,不僅是道給即將離開的人, 也是道給他在人生旅途中積攢下來的點點滴滴。 阿爾茨海默病緩緩奪走一個人生命的過程被我的母親稱為“漫長的告別”。這是她公開發表過的少有幾句評論之一。面對論及我父親健康狀況的話題,我們一致選擇了用畢恭畢敬的沉默來掩飾。這是一種令人心碎的說法。她告訴我,自己再也不會重提這句話了,因為它催人淚下。 我剛剛結束《天使不死》的巡回售書活動,沒有多少時間顧得上流淚。在飛機和陌生的酒店房間中,我一有空就睡覺,在根本沒有機會整理的行李箱中飛快地東翻西找,從一個采訪奔赴另一個采訪。絕大多數采訪都是友好的,充滿了鼓勵的意味。成為一名作家、將自己置于風口浪尖是我的選擇。我都不知道自己在歷次的巡回售書“戰役”中是如何幸免于難的。可以想見,即便是*順利的巡回售書活動,也總會有一場采訪令你對采訪者的粗魯迷惘地搖頭。 事情發生在一座小城市里。城市的名字我就不提了。那是一場午后的脫口秀節目。節目主持是一個想成為卻永遠成不了奧普拉的女人。她開口詢問了我父親的狀況。針對這個采訪問題,我的答案一成不變。“他很好。”我說,“在涉及他健康狀況的問題上,我的家人需要保留隱私。不過他很好。” 這樣的答案通常就已足夠,誰也不會進一步逼問。“那他還記得你嗎?你能和他對話嗎?”她顯然認為,問幾句我已明確表示不會回答的私人問題是完全合理的。 “如我所言,我們需要保留隱私。我覺得我們有這個權利。” “你們具體是什么時候發現他得了阿爾茨海默病的?是不是開始注意到他會忘東忘西,或是把事情搞混?” “我已經明確說過了,你問的這個問題我不會回答。”我的語氣更強硬了。我能感覺到現場觀眾的尷尬。她卻又試了一次。 “現在和他對話是什么感覺?你都會和他聊些什么?” “這是我第四次也是*后一次給出同樣的答復了。我們需要隱私。無論你用多少種不同的措辭問相同的問題,我都不會回答你的。” 觀眾鼓起掌來。她終于把話題轉移到了另外一系列的問題上。 節目結束后,當我急匆匆地走向出口時,她開口說道:“我希望你能理解,我只不過是在盡一名記者的責任。” 我想我沒有搭理她。 巡回售書的另一個難處雖然有些悲哀,但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也是甜蜜的。一次又一次,在談及父親和我為他寫的書時,我都會沉浸在記憶的榮光中,想起他忠實的信仰和講過的故事中飽含的精神食糧。“漫長的告別”這句話時常在我的腦海中低語,如同一縷清風穿過敞開房門的屋子。我想流卻沒空流的眼淚在心里積成了一汪池水—耐心等待我靠近、深不見底的池水。回到紐約,我一心只想睡覺和哭泣。 在某種程度上,這趟巡回售書讓我能夠直面自己迄今為止的生活,直面自己過去的選擇,直面我與父母經年的斗爭。采訪前,我會在演員休息室給母親打電話,或是在酒店房間和機場里撥通她的號碼。她現在已經成為我生活的一部分。但我還是能夠看到,那些年的放逐如同荒原般在我的身后鋪展開。 名望是一種奇怪的東西,即便你是伴隨它長大的,也還是會被它驚得目瞪口呆。你以為自己已經對它了若指掌,能夠按順序安排好輕重緩急,思維清晰地做出選擇,但大多數人都會犯錯。我覺得聚光燈**次照在你身上的那一刻才是*重要的。沒有哪個錯誤能比那一刻犯下的錯誤更加嚴重。它是個黃金時刻,并且永遠不會重來。其他的時刻還會到來—我不相信我們只有一次機會能把事情做好—但永遠不會再那般純粹、毫無負擔。 父親當選總統那年,我28 歲。盡管對人們強烈的關注并不陌生,但我們還是陷入了媒體的旋渦中。顯然,這一切都是因為我的父親,我們其余的人也處在了聚光燈下。我犯下的**個錯誤就是以為自己能夠應付一切。要是我能多一些猶豫,少一些篤定,就能多提幾個問題,思考更多的選項。結果,陪伴我前行的卻是對自身政治信仰極度的熱誠。我曾在大型反核集會上發言,接受采訪,把自己塑造成了父親的政策*引人注目的反對者之一。要是我能多一些外交手段,少一些尖銳的言辭,其實本可以成為父親與自由主義觀點之間的橋梁。相反,即便是在那些與我持相同政治信仰的人眼中,我也不過是個憤怒的女兒。 宣泄完*初的憤怒,我又開始表達更加私密的情感,把在全世界面前展示我家庭的創傷視為己任。我的怒火招致其他人的憤怒。說我收到過恐嚇信,那是輕描淡寫。 這些問題大多是在巡回售書的過程中顯露出來的,我其實很難擺脫自己的過去。每個人都在成長、轉變和學習,但在公眾的矚目下經歷這一過程會更加艱辛。大多數人都是寬容的,但我能從他們的眼神中看出,記憶是長久的。這就是在公眾的目光中成長的難處:你永遠處在別人對你的記憶之中。 在我的想象中,我會和父親談論此事,告訴他我多希望自己當初能以不同的方式去應對發生過的一切。也許對于我們每個人來說,針鋒相對的觀點可以是一種啟示,而不是一場戰爭。在我的想象中,他的眼中閃爍著光芒,微笑地說著“我很高興我們現在可以討論這個問題了”之類的話。然而這段對話只能發生在我的想象之中。在現實生活中,他身上可以參與對話的那一部分已經遠去了。 碰上阿爾茨海默病之類的疾病,荒涼的感覺也會屬于患者的朋友和愛人—那些見證了過程還要被丟下暗自神傷的人。你會眼睜睜看著一個人退到某個陌生的地方,心知自己無法跟上。失去他,你將一個人在荒野中徘徊,耳邊回響著山坡上傳來的回音。那只是回音—聲音傳來的地方越來越安靜—于是你會更加仔細地聆聽。 如今,母親的很多話都是以“我記得……”開頭的。 你之所以會為自己的記憶注入生機,是因為就在那里、就在你的眼前,坐在他過去經常坐著的椅子上,或是走在樓道里,抑或凝視窗外時,你都會想起往事。記憶被抹除后,剩下的就是一片空白,因此,每當想起某些畫面或是只言片語,你都會欣然接受,緊緊抓著它們,拂去上面的灰塵,期待它們能永遠鮮活。 現在,我時常想起父親講過的故事,希望能再聽到他講故事的聲音,看到那雙可以激活孩子的想象力、閃爍著喜悅光芒的藍色眼睛。但我只能依靠回聲來滋養自己。我想要他再告訴我一次,鷹與禿鷲的區別。它們的飛行軌跡、翅膀存在細微的差異。其中一種在朝獵物俯沖前會多盤旋一會兒。我過去常把它們弄混。要是我們在牧場上發現了二者中的任何一種,他就會耐心地為我一遍遍解釋說明。我還是會把它們弄混,但我已經不能再問他了,因為他也記不得了。我想和他騎上馬,朝著翠綠的山坡飛馳,可他已經永遠無法再騎馬了。 一次,在前往牧場的途中,車子正沿著穆赫蘭道行駛。他停下車,對山坡上的一個男人說,他正在采摘的藍羽扇豆是受保護植物。父親解釋得彬彬有禮,于是那個男人從山上爬了下來,手中卻仍攥著非法采來的花朵。父親相信,只要有可能,鮮花和野生動物都應該留在它們的應屬之地。我五歲那年便能認出響尾蛇,知道要繞一個大圈才能躲開它們。我還知道,除非萬不得已,否則絕對不能殺害一個生命。 我從未如此深切地渴望過童年—哪怕只是嘗上一口,都如舌頭上的威化餅,成為我與已然失之交臂的過去甜蜜的交流。成年人會帶著可悲的智慧回首往事,想起兒時的我們是何等幸福,根本不知道人生在邁著堅定的步伐前進,也不知道歲月在倒數計時,仿佛時間不可能在我們的肉體上刻下痕跡。驀然回首,我們才希望自己能夠更好地把握某些時刻,久久凝視某個人的面龐或是壯觀的夕陽,更仔細地聆聽某個終有一日會歸于沉寂的聲音。我們還希望自己走得再慢一些,徘徊得再久一點兒,踏上不同的道路。我們將大大小小的往事儲存在記憶中,期盼它們不會破碎或褪色,因為它們是我們活過這一世的見證。 與所愛之人道別,那句再見,不僅是道給即將離開的人,也是道給他在人生旅途中積攢下來的點點滴滴。我的父親正邁著堅定的小步遠離曾經的自己。我不知道還能從他身上學到什么東西—有關土地、馬兒、鳥兒的飛行軌跡,還有只能在某些區域茁壯成長的植物。在牧場的橡樹林里,他曾找到過一種打濕后會像肥皂一樣起泡的植物。 他相信,要讓孩子們為生活中的災難做好準備,否則這些波折和突變有可能帶來毀滅性的結果。他會為我們設定幾個情景,問我們打算怎么應對,然后溫和地糾正我們。這樣一來,就算災難降臨,知識也能成為我們的盟友。 有一次他問我:“如果你的臥室起火,房門卻被堵住了,你會怎么做?” 看過無數電影的我回答:“我會沖破房門。” “那你就沒命了。”父親冷靜地回答,“你剛走到距離火苗不到兩英尺的地方,就會被熱氣灼傷肺部。” “那我就打破玻璃,跑到院子里去。” “好的。”他點了點頭,“你怎么打破玻璃?” “用一把椅子。” 我總是能夠清楚地分辨出,課程*重要的一部分何時到來。父親會俯下身,用緩慢而謹慎的語氣對我說話,迫不及待地希望自己的話能在我的心里生根發芽。“你可以拿出一只抽屜,把它從窗戶里推出去。”他告訴我,“這樣就能形成一個整齊的缺口,不會在你爬出窗戶時將你割傷。” 他讓我為火災、空襲警報和地震都做好了準備,卻沒有讓我準備好失去他,沒有給我工具去應對滿腔悔意的沖擊。我后悔自己厭惡他的那段時光,后悔曾甩掉他伸出的手,選擇了如矛刺般尖銳的言語。那些都是深埋在我心里的記憶。如果還有什么補救的辦法,那么我還沒有找到。 失去父親或母親的故事中通常都包含著發現的過程。打開一只抽屜、一本書、一盒信,你便能知曉從前并不了解他們的地方。他或她在喜歡的書本空白處潦草地寫下想法,或是你無意中發現某封信。有些時候,我們是在父母去世后才了解他們的。我的母親一直在收拾抽屜—我想,她應該是有意這么做的,因為她知道我們的生活有一部分是公開的,要面對全世界窺探的目光。她想要知道別人會發現什么。在父親的其中一只抽屜里,她找到了給我的一封信。那是一份草稿,尚未寄出,是在我的自傳出版前寫下的。信中,他表示自己被我的怒火傷透了心,也表達了家庭和解的愿望,還有他對更多美好時光的記憶。信的開頭,他寫道“隨著我年近八十一歲……”然后又劃掉了自己的年齡,在上面寫了一行“如今我已經八十一歲了……” 我想象,在日子緩慢流逝的過程中,他也許曾無數次拿出這封信,感覺自己的生命已所剩無幾。我永遠都無法知道他多久便會把它拿出來添上幾筆,再重讀一遍,也不知道他為何永遠不曾將它寄出。在信的末尾,他寫道:“求你了,帕蒂,別帶走我們對那個真心疼愛、心心念念的女兒的回憶。” 如今,這封信已經被放進了我的抽屜,陷入了無邊的沉寂。我多希望自己能和他聊一聊它,然而他對它的記憶可能已經消失在了地球的邊緣。 人們離世時都會帶走自己隱藏的秘密—燭光閃爍的歡樂記憶、支離破碎的悲傷記憶。他們離開了,記憶也將隨之而去。我們剩下的人則會被丟在黑暗中,懷抱著再也沒機會提出的問題,和想說卻說不出口的話語。因為我們來得太遲了。 講述這場“漫長告別”的任務已經落在了我的身上。盡管這些日子并不沉重,卻還是需要被記錄下來,因為它們珍貴萬分。我們跨越苦痛去尋找救助,雙手如同伸向圣杯,充滿渴望。我們碰不到它,卻知道它的存在。我還精進了忍住眼淚這門藝術,像只驕傲的野獸,將淚水儲存起來,然后退回我的洞穴,好給它們應有的地位,尊重其與生俱來的權利。這段漫長的旅程就是曾經似乎縫合在一起的確定性—我們在另一個人身上了解到的一點一滴—逐漸分崩離析的過程。你會習慣這樣的疾病帶來的驚喜,習慣那些令人困惑的短語,習慣突如其來的轉折。你不指望什么,但已經可以在熟悉的環境中更加自如地呼吸。這將永遠是一場等待的游戲。 即便沒有疾病帶來的并發癥,對于年逾八十的人來說,人生的隧道也越來越窄。多年前,父親在給我寫信時就已經有了這種感覺。有些時候,我很想知道事情會在何時發生,我何時才會得到消息。半夜嗎?黎明嗎?無論是什么時候,我都十分清楚,父親的離去將是一段平靜的旅程。 昨天,我在針灸師的床上睡著了,身上各處經絡上插著活血化瘀的針,墜入了漆黑一片的深度睡眠中,身陷緊張得令人心驚肉跳的鮮活夢境。我看見父親從身體里邁了出去,離開八十四歲的自己,成了一個更加年輕、更有活力的男子,臉上還帶著燦爛的微笑。他生龍活虎、熱情洋溢地張開雙臂,走向我的母親,安慰她一切都會好的。 盡管一切終將有所不同,但都會歸于平靜。擺脫了悲傷、恐懼與無情的苦痛,生活將進入某種模式。就眼下的情況而言,生活就是等待。這就像是在閃電后數秒,等待你知道必將到來的雷鳴,試圖預測風暴還有多遠。
漫長的告別 作者簡介
帕蒂·戴維斯(Patti Davis),原名帕特里夏·安·戴維斯·里根,美國前總統里根最小的女兒,里根與南希·里根WEIYI的女兒,演員,作家,模特。著有《我的視角》《天使不死》。她的許多文章被刊登在《時代》《新聞周刊》《時尚芭莎》《名利場》《城鄉之間》《華盛頓郵報》《洛杉磯時報》上。 帕蒂·戴維斯曾經以叛逆著稱,以各種出格的行為與父母對抗,就連帕蒂·戴維斯這個名字也是她為了抹去父親和家族的烙印而取的藝名。
- >
二體千字文
- >
羅庸西南聯大授課錄
- >
月亮虎
- >
羅曼·羅蘭讀書隨筆-精裝
- >
煙與鏡
- >
【精裝繪本】畫給孩子的中國神話
- >
推拿
- >
史學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