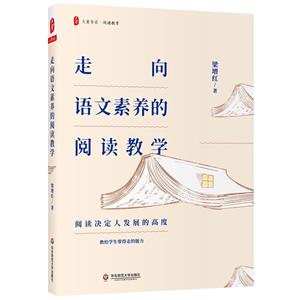-
>
山西文物日歷2025年壁畫(特裝版)
-
>
老人與海
-
>
愛的教育
-
>
統編高中語文教材名師課堂教學實錄
-
>
岳飛掛帥
-
>
陽光姐姐小書房.成長寫作系列(全6冊)
-
>
名家經典:水滸傳(上下冊)
大夏書系 :走向語文素養的閱讀教學 版權信息
- ISBN:9787576012736
- 條形碼:9787576012736 ; 978-7-5760-1273-6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大夏書系 :走向語文素養的閱讀教學 本書特色
閱讀決定人發展的高度,教給學生帶得走的能力。 ☆語文特級教師梁增紅全新力作,創意閱讀教學好助手。 ☆閱讀素養是學生從小學開始就應該掌握的重要能力,是中小學生精神輸入的基本途徑,也是基本的成長方式,閱讀決定著一個人發展的高度。 ☆既有對閱讀教學的理性思辨,又有對經典名篇的示范教學,閱讀教學新理念+新方法助力語文教師有新提升。 ☆作者從閱讀教學解讀、閱讀教學場景、閱讀教學思辨三個方面,分享了他發展學生語文素養的教育理念、創意策略和理性思考。 ☆語文教學中,語言學習需與精神成長共舞,實現“立言立人”,把學生精神成長作為教育的旨歸。 推薦篇目: P59 不教什么:從“細讀”到“細教”的追問 P86 自讀課文:閱讀教學的另一半 P148 單篇教學咋就成了“過街老鼠” P190 閱讀教學不是做“證明”題
大夏書系 :走向語文素養的閱讀教學 內容簡介
語文特級教師梁增紅結合自己多年的語文教學實踐,從閱讀教學解讀、閱讀教學場景、閱讀教學思辨三個方面,分享了自己在閱讀教學中促進學生語文素養發展的教育理念、實施策略和理性思考。作者把學生精神成長作為教育的旨歸,在閱讀教學中帶領學生徜徉于語言文字中,用生命去體驗、用心靈去感悟、用言語去表達,逐漸形成和提升學生的人生觀與價值觀,實現“立言立人”。
大夏書系 :走向語文素養的閱讀教學 目錄
教學解讀:將“作品”轉化為“課文”/003
語文課導入“三忌”/010
語文教學中情境創設的誤區及對策/016
品讀關鍵詞,探究文本義/023
審美:文學作品教學的核心/031
文本的教學解讀要有“三度”/041
句子有密碼,妙處與君說/051
不教什么:從“細讀”到“細教”的追問/059
分享語言:散文閱讀教學的關鍵/066
細品標點滋味長/071
關于波折的教學路徑摭談/079
自讀課文:閱讀教學的另一半/086
閱讀教學:走一步,再走一步/090
第二輯 閱讀教學之場景:語文素養發展的實然路徑
例談小說閱讀方法指導教學
——我教《貓》 /099
朗讀要“得他滋味”
——我教《雖有嘉肴》 /108
自讀課,教師要克制“講的沖動”
——我教《一棵小桃樹》 /114
提挈“三個一”,指向“兩個一”
——我教《周亞夫軍細柳》 /123
“黃金配角”也重要
——我教《范進中舉》/130
教出“這一篇”的特性
——我教《昆明的雨》/135
第三輯 閱讀教學之思辨:語文素養發展的本然選擇
“互聯網+語文”還是“語文+互聯網”/145
單篇教學咋就成了“過街老鼠”/148
當學生拿著參考書回答問題/153
好課借鑒:變“暗中摸索”為“明里探討”/155
教學有套路,不可陷太深/159
老師,我不喜歡紫藤蘿花/163
喜歡或不喜歡,課文都要教/166
咬文嚼字豈可廢/169
語文教學:豈會立竿見影/173
語文教學的“干貨”在哪里/177
語文教學:不要“借助PPT而一頓胡扯”/182
語文教學:怎能讓理性缺席/185
閱讀教學不是做“證明”題 /190
戲說經典當休矣/197
“語文味”是什么味/201
作品形式不容忽視/205
不要讓學生把知道的內容大張旗鼓地再說一遍/208
裝神弄鬼何時休/211
多一些“各人各讀法”/215
不妨“聽聽”自己的課/219
大夏書系 :走向語文素養的閱讀教學 節選
教學解讀:將“作品”轉化為“課文” 李海林先生認為,語文教材具有原生價值與教學價值的雙重屬性。他說:“語文教材是由相互之間在內容上沒有必然聯系的若干篇文章組成的。這些文章,原本并不是作為教材而編寫的,而是作為一種社會閱讀客體存在的。它們原本作為社會閱讀客體而存在的價值,可稱之為‘原生價值’。……但是,這些文章一旦進入語文教材,它們的價值就發生了增值和變化。它們保留了原本所有的傳播信息的價值,同時又增加了一種新的價值,即‘如何傳播信息的信息’,這種‘如何傳播信息的信息’即我們所謂的‘教學價值’。” 因而,語文教學不能僅僅滿足于對文章原生價值的闡釋,更應該在此基礎上充分挖掘其中隱含的教學價值——教學生學習文章傳遞信息的方法、策略,讓學生明白文章是如何講的,進而實現將文本原生價值轉化為教學價值。 一、文本的原生價值,既有作者的原意,也有讀者的二度創作 說起文本的原生價值,常有人狹隘地理解為作者的創作“本意”。其實,原生價值不僅包括作者的創作本意,還包括讀者在閱讀過程中的二度創作。這就使得文本的原生價值,具有多種解讀的可能。 以前有一個被人熱議的現象,說某位作家的作品,被用在語文考試中,結果發現試卷中的一些題目“自己也不會解答”,甚至主題往往不是自己當初所想的。這種現象曾引起一片嘩然,很多人以此為據,譴責中高考試題出得怪異。其實,分清了文本的原生價值與教學價值是有所不同的,就不難理解上述現象了。安伯托??艾柯說:“一切閱讀都是誤讀。”讀者的解讀,與作者的創作原意也許相同相近,也許交叉,也許背道而馳。作家的作品,一旦問世,其意義往往由作者、文本和讀者來共同完成,有時“作者未必然,讀者未必不然”。 所以,語文教師教學時如果費盡心思想追索作者的原意,往往是徒勞無益,幾乎是不可能的。因為唯一有說服力的就是作者本人所說,作者為自己的文章留下了一些明確的表示。盡管這樣,有些作者把自己的創作意圖公之于眾,也不能阻擋讀者有自己的再創造,不能左右讀者的閱讀思路,不能保證所有讀者與作者的初衷完全疊合。魯迅先生在講授他的《中國小說史略》時說:“《紅樓夢》是中國許多人所知道,至少,是知道這名目的書。誰是作者和續者姑且勿論,單是命意,就因讀者的眼光而有種種:經學家看見《易》,道學家看見淫,才子看見纏綿,革命家看見排滿,流言家看見宮闈秘事……”那么多的“看見”中,哪一個是曹雪芹本人的創作初衷呢?恐怕除了曹雪芹本人,其他解讀都是讀者的建構了。 王國維《人間詞話》中的“三境界說”是典型的例子: 古今之成大事業、大學問者,罔不經過三種之境界:“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此**境界也。“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界也。“眾里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此第三境界也。 這三處引用詩詞,分別指立志、刻苦奮斗、水到渠成達成目標,自然都不是本義,任何一個對古典文學稍微有所了解的人都不至于由此認定原詞的意思就是這樣。王國維自己也承認“然遽以此意解釋諸詞,恐為晏、歐諸公所不許也”。但是,這一引用新奇有趣,傳達出了深刻的人生哲理,也得到了廣泛的認可。真是“今人不見古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正因為閱讀的過程實際上都是再創作的過程,這種創造如果能夠貼切地用于當前生活,又不至于引起他人對古詩詞的誤解,就有其價值。換言之,在文本解讀上膠柱鼓瑟并不可取。 如“所謂伊人,在水一方”,起初人們把其中的“伊人”認定為情人、戀人,詩歌表現了抒情主人公對美好愛情的執著追求和追求不得的惆悵心情。然而在后人的解讀中,早已不再局限于“愛情”主題,而是生發出更有價值意義、更令人共鳴的東西:“在水一方”——“可望難即”這一具有普遍意義的藝術意境。由于詩中的“伊人”沒有具體所指,而河水的意義又在于阻隔,所以凡世間一切因受阻而難以達到的種種追求,都可以在這里發生同構共振和同情共鳴。類似的還有“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干”“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春色滿園關不住,一枝紅杏出墻來”等。 從這個意義上說,閱讀教學中,師生在理解文本的意義上,應當貫通古今,盡力探求本義,在具體的應用上則不需要太過于執著本義,苦心孤詣地思索作者“原意”,而應該以語言文字為支點,靈活生發,古為今用,讓文本搖曳生姿、常讀常新。否則,縱然皓首窮經,焚膏繼晷,也無法曲盡其妙。 比如,莫懷戚在《〈散步〉的寫作契機》中說了自己的創作動機和想表達的宗旨: 這篇文章寫作的契機,現在回想,應該是兩個。 **個就是一次全家三輩四口人的散步,的確如文中所說:初春,南方的原野,哄了一陣才將母親帶上路……當時我兒子正上幼兒園,他叫“前面也是媽媽和兒子,后面也是媽媽和兒子”也是真的。但是當時我們的笑,是為小家伙的出語機靈而興奮,像所有年輕的父母一樣,以為自己的孩子是天才,或者至少也有過人之處──你看他小小年紀便懂得歸納,將來豈不是個哲學家? 第二個契機則較有理性色彩。我與來西南政法學院進修中國民事訴訟法的美國漢學家柯爾特先生相熟后,常就中西文化的異同進行淺層次交談。出我意料的是他對中國文化中的“孝悌”的看法──他將其拆開,反對“悌”(他說弟弟沒有必要高看兄長),而對“孝”,卻大加贊賞,說中國人的敬老愛幼,是“文化的精髓”,又說英國哲學家培根說過,“哺育子女是動物也有的本能,贍養父母才是人類的文化之舉”,這個,全世界數中國人做得*好,云云。他還同我一起看過中央電視臺舉辦的春節聯歡晚會,說這種“由政府出面召集,全國像一家人在過年的事,在美國是不可想像的”。 雖然作者有此一說,但不影響讀者們因生活經驗、閱讀能力而產生的種種解讀。在實際教學中,我們發現關于《散步》的主旨解讀,有關于“孝”的,有關于“生命”思考的,有關于“中年人的責任與使命”的,有關于“親情”的,有關于“尊老愛幼”的,等等。師生之所以有話可說,是因為文本中存在著多種解釋的可能,教學中要做的不是自我封閉,或者將某種說法定于一尊,而是要努力形成一種對話的氛圍,通過恰當的話語時機和方式,把問題說清楚。 二、發掘文本的教學價值,實現“作品”到“課文”的轉換 魯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說來》中說:“自然,做起小說來,總不免自己有些主見的。例如,說到‘為什么’做小說罷,我仍抱著十多年前的‘啟蒙主義’,以為必須是 ‘為人生’。而且要改良這人生。……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態社會的不幸的人們中,意思是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他又在《〈吶喊〉自序》中說:“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所以我們的**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他在談到《阿Q正傳》的成因時,說他要“寫出一個現代的我們國人的魂靈來”。他又說:“我雖然竭力想摸索人們的魂靈,但時時總自憾有些隔膜。在將來,圍在高墻里面的一切人眾,該會自己覺醒,走出,都來開口的罷,而現在還少見,所以我也只依了自己的覺察,孤寂地姑且將這些寫出,作為在我的眼里所經過的中國的人生。” 魯迅先生的這番自我表述,道出了他寫小說的意圖。由此觀之,作家(作者)創作一篇文章,其原生價值或為了讓人獲取信息,或為了讓人怡情養性,或為了抒發某種情感、表達某種觀點,極少是為了直接用來教學的,也就是創作目的是為了“做教科書”的(據我有限的了解,除朱自清的《春》屬于此類外,未有所聞)。正如魯迅先生在談及《紅樓夢》時所說這么多的“看見”,是否都適合用來“教學”?當然是不現實的。這就需要從文本的原生價值中,發掘教學價值,使之發揮教學作用。這個過程,就是文本的教學解讀的過程。 比如,王榮生教授把文本分為“定篇”“樣本”“用件”“例文”四類。他所說的“定篇”,也就是“經典”文本,則側重于“人文性”,而不是“工具性”: 當“定篇”教的課文,是文學、文化的經典,或素有定評的名家名篇,比如魯迅的作品、語文教科書中的古詩文。學生學習這些課文的主要任務,就是熟知經典,透徹地領會課文本身,從而積淀為文學、文化的素養。換言之,學生的學習任務,是深入地理解、感受這些經典名篇,理解和感受它們何以是經典,理解和感受它們超越時代的思想、情感和杰出的藝術表現力。“定篇”的教學,離不開讀與背,但不能止于讀與背。關鍵是要真切地領會,切身地理解它歷經淘沙的魅力,乃至偉大。 一般說,經典作品明顯高于學生的語文經驗,包括他們的生活經驗和思想水平,要使學生真切領會,往往要借助于外力。外力包括創設易于理解和感受的情境(有時要借助于多種媒介),提供對理解和感受有促進作用的權威的解讀資料,提供構成互文的相關作品,以及語文教師在切身感受和較充分參考研究資料基礎上的講解。 王榮生教授的想法,其實與朱自清先生的觀點相一致。朱自清先生在《經典常談》中說:“在中等以上的教育里,經典訓練應該是一個必要的項目。經典訓練的價值不在實用,而在文化。有一位外國教授說過,閱讀經典的用處,就在教人見識經典一番。這是很明達的議論。再說做一個有相當教育的國民,至少對于本國的經典,也有接觸的義務。”也就是說,像經典文本的教學,大致可以不必執著于“訓練”,重點在于“文化”,在于“教人見識經典一番”,說側重于原生價值也不為過。當然,如果讓學生既能讀出原生價值,又能觸摸教學價值,則皆大歡喜。如《孔乙己》等,不僅讓學生讀到“一般社會對于苦人的涼薄”,又能從中咀嚼出“排”“摸”“走”“笑”等細節的教學價值,那么,對于學生的語文學習則是善莫大焉。 可惜,這樣的完美的經典作品畢竟難得。一般情況下,只能采取有所側重的原則。文本的原生價值包羅萬象,見仁見智,我們用來教學,要像2011年版新課標中指出的那樣:“義務教育階段的語文課程,應使學生初步學會運用祖國語言文字進行交流溝通,吸收古今中外優秀文化,提高思想文化修養,促進自身精神成長。工具性與人文性的統一,是語文課程的基本特點。”我狹隘理解,文本的原生價值側重于“人文性”,而文本的教學價值則側重于“工具性”。 請注意,我這里所說的是“側重”,而不是“非此即彼”。 比如,有人說《水滸傳》不適合學生讀。不可否認,其原生價值中有許多東西,的確已經不合時宜。不單是《水滸傳》,任何一個文本,都有其良莠不齊、泥沙俱下的內容,要說“不適合”學生,如果睜大眼睛去挑剔一下,估計就不會有合適的書了。這就需要進行文本的教學解讀,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從中選擇合適的“精華”內容,讓學生有明確的目標去讀。毋庸置疑,讀《水滸傳》,一定會讀到打打殺殺、報仇雪恨之類的“糟粕”,那當然是不合適學生了。我們應該鼓勵學生讀什么?一是讀到一些英雄情結,尤其是那種路見不平一聲吼的氣概。二是從語用的角度,去關注小說中的人物描寫、情節設置等,如《水滸傳》中武松打虎波瀾起伏的故事情節、魯提轄拳打鎮關西的動作描寫等,也就是說,如果從學習語文的角度來看,語用是**重要的,因而我們不妨引導學生多關注小說中的“語言形式”。金圣嘆在《讀第五才子書法》中說:“吾*恨人家子弟,凡遇讀書,都不理會文字,只記得若干事跡,便算讀過一部書了。”王尚文先生說:“‘理會文字’,我以為就是關注語文品質,品味作品如何遣詞造句、謀篇布局,也就是弄懂弄通其字法、句法、章法。字、句、章相關相連,字法、句法是基礎,但也離不開章法,而章法也要靠字句體現出來。” 當“作品”轉化為“課文”的時候,文本便具有了教學價值。語文老師需要做好從文本的原生價值中遴選出合適的內容發掘教學價值的轉換工作。這樣,“用教材教”而不是“教教材”,才有可能落到實處。此所謂文本的“教學解讀”。
大夏書系 :走向語文素養的閱讀教學 作者簡介
梁增紅,江蘇省中學語文特級教師,正高級教師,常州市突出貢獻人才,常州市教育領軍人才,教育部專題課程主持專家,“國培計劃”特聘專家。應邀赴全國各地做講座或上公開課100多節次,在《人民教育》《中學語文教學》等期刊發表100多篇教育教學論文,出版個人專著2部,主持完成省級課題2項。《語文教學通訊》《基礎教育課程》《江蘇教育》《浦東教育》《師道》等刊物封面人物或專訪名師。現任教于江蘇省常州市第二十四中學。
- >
伯納黛特,你要去哪(2021新版)
- >
龍榆生:詞曲概論/大家小書
- >
小考拉的故事-套裝共3冊
- >
隨園食單
- >
莉莉和章魚
- >
自卑與超越
- >
大紅狗在馬戲團-大紅狗克里弗-助人
- >
名家帶你讀魯迅:故事新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