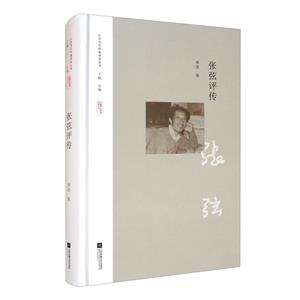-
>
魯迅全傳:苦魂三部曲-增訂版(全三冊)
-
>
大家精要- 克爾凱郭爾
-
>
尼 采
-
>
弗洛姆
-
>
大家精要- 羅素
-
>
大家精要- 錢穆
-
>
白居易:相逢何必曾相識
張弦評傳 本書特色
20世紀八九十年代文壇和影視圈才子的一生,研究張弦生平及創作成就的必讀資料。 著名劇作家、作家張弦評傳,考據嚴謹、資料詳實,全面梳理張弦一生創作成就,學術性與可讀性俱佳。 蘇州大學文學院季進教授撰寫,附張弦珍貴照片。
張弦評傳 內容簡介
《張弦評傳-江蘇當代作家評傳叢書》是一部關于著名作家及編劇張弦的傳記。張弦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具有很高的社會能見度,一生創作的作品無數,《被愛情遺忘的角落》《楊貴妃》《唐明皇》《金鏢黃天霸》等均是他耳熟能詳的作品。張弦擅長從女性視角切入,善于描寫女性細膩的感情和特質。該書利用豐富的一手資料,詳盡還原了張弦的一生,展現了在大時代潮流中一個生命個體的平凡和不平凡。 該書予評予議,給張弦以合適的文學史定位。
張弦評傳 目錄
第二章 在青春激情中起步
第三章 受難與復出
第四章 風靡一時的小說創作
第五章 走向成熟的小說創作
第六章 雙線分合的精神探索
第七章 “墜入電網”的靈魂書寫(上)
第八章 “墜入電網”的靈魂書寫(下)
張弦文學創作年表
后記
張弦評傳 節選
《張弦評傳-江蘇當代作家評傳叢書》: **章 坎坷的人生之路 20世紀30年代的上海,已經發展成為一個繁華的國際大都市,也是當時中國*大的通商口岸,一個充滿著現代性魅力,同時又保留著東方情調的遠東都市,被稱為“東方巴黎”和“冒險家的樂園”。1934年6月22日(農歷五月十一日),張弦就出生于上海福煦路,原來名叫張新華,“張弦”是后來寫作時所取的筆名,如今原名早已被人們淡忘。 張家的祖籍其實是杭州,并非土生土長的上海人。張弦從小就知道“上有天堂,下有蘇杭”的說法,后來填寫履歷表時,總是自豪地寫上“浙江杭州人”。他的父親張祖蔭,是前清道臺府的一個幕僚的兒子,一生都在黑暗的官場中討生活,目睹了太多的殘酷的官場爭斗,所以臨死前千叮萬囑不準兒子再當官。于是,張弦父親很早就進了洋學堂,學習西方知識,主攻化學,學成之后,懷抱著“實業救國”理想,開過工廠,辦過鐵路,可惜都沒成功,破了產,“實業救國”的夢也徹底破滅,20世紀30年代初,張弦父親到上海中國銀行當會計主任,過起了老百姓的小日子。他父親的前妻生下兩男一女后就去世了,他父親在五十三歲的時候續弦,娶了浙江南潯的一個小蠶絲廠廠主的女兒。她母親自幼喪父,從小就在開絲廠的伯父家長大,也上過洋學堂,接受過新式教育。由她伯父作主,嫁給了比她大三十歲、有三個子女的張弦父親續弦,但他母親對此似乎頗為滿足,從無怨言,對他父親一直以“少爺”相稱,從來不叫名字,這讓年幼的張弦十分納悶。父母親結婚的第二年,張弦呱呱墜地。張弦自述,他的記憶中不記得有過什么幸福的童年,也許三歲以前的孩提時代,有過一段優裕而歡樂的日子,但隨著抗日戰爭的爆發,全家人四處流浪,居無定所,從此就在兵荒馬亂中度過了自己的童年。 1937年11月12日,日軍侵占上海,上海淪陷。除了城市中心公共租界的中區、西區和法租界日軍尚未進入之外,上海四周都已為淪陷區所包括,形成了所謂的“孤島”。當時日本同歐美各國尚未交戰,上海租界里依舊是燈紅酒綠,太平盛世。1941年12月8日,日軍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正式向英美宣戰,進駐上海租界蘇州河以南區域,把這些租界內的西方公民圈入集中營,至此上海全部淪陷,“孤島”時期宣告結束。全面淪陷后的上海市民,也陷入了無比恐慌的狀態,物價飛漲,生活無著,戰爭威脅,許多市民開始紛紛逃離。也就在這個時候,張弦父母帶著全家老小,走上了逃難之路。兩個哥哥在途中奔向大后方參加抗戰去了,后來都成了國民黨機關的職員。父母帶著姐姐和張弦經過南京跑到了安徽的蕪湖,后來生活還是無著,不得不又經南京,重新回到淪陷后的上海。在上海,全家人的日子也不好過,原來的銀行已搬遷,父親找不到工作,全靠原來的一點家底硬撐著,撐了沒有多久,實在撐不下去了,全家只得又再次遷回南京。這個時候,張弦已經七歲了,已在上海讀了兩年小學。汪精衛偽政府成立后,南京形勢略有平定,父親終于在汪偽政府的“財政部”謀到了一個會計的職位,收入微薄,只能維持全家的*低生活,勉強度日。在張弦的童年記憶中,他父親總是一張陰郁的臉,唉聲嘆氣,牢騷不斷,肺病也越來越嚴重,到南京的第二年,就不幸去世了,那年張弦才九歲。張弦的外公早逝,外婆在他父親去世前,也來到南京與全家生活在一起。父親去世的第二年,外婆也去世了。從此,南京成了張弦不是故鄉的故鄉,給他后來的生活與創作都留下了深刻的影響。“我在她懷抱里成長。離開了她而終又未能遠去。她給過我可怕的噩夢,也給了我理想的晨曦,初春的芳馨。別時,她使我魂牽夢繞;相見,我又不能不寄以深切的期望。”這是*好的城市,也是*壞的城市,美好與恐怖的記憶并存,兩極化的生活體驗都曾有過。“相處如同陌生,闊別卻又覺得親。” 一個曾經的大家庭,經此變故,完全陷入了困頓。父親病故,兩個哥哥早已離家去了大后方,母親獨自撐起了這個家庭。母親學會了打字,當了打字員,又給姐姐謀了個雇員的職業,以兩人微薄的工資養活外婆和張弦,生活十分清苦。有一年夏天,家里來了客人,母親買了個西瓜招待客人。這大概是張弦童年時**次吃西瓜,吃相不雅,一粒瓜子吞落下肚,就驚慌地哭叫起來,弄得母親很難堪。客人走后,挨了母親狠狠的一頓打。與母親、姐姐以及外婆一起生活,讓張弦從小就感受到來自女性的寵愛,而她們的哀傷和愁苦,也對他幼小的心靈產生了很深的影響。特別是母親,比他父親小三十歲,三十三歲時就守了寡,母親的痛苦張弦也許小時候不理解,但成年之后,他會常常回憶起來,深為同情。這些潛在的意識和感性認知,也許成了張弦特別關心婦女命運的主要原因。 張弦的童年與少年時代,一直處在一種國難家仇的艱辛環境之中。南京沒有給他以溫柔的歌聲,相反,回響在耳邊的是日本憲兵隊的可怕足音,還有父親病重時的痛苦呻吟和母親無望的痛苦哭泣之聲。當然期間也不乏美國軍用吉普刺耳的喇叭聲,新街口倒賣銀元牟取利益的錢幣販子手中叮當作響的聲音,以及國大代表競選的政治鬧劇中念誦候選人名單諸如“孫科、李宗仁……”的唱票廣播。此外,尚有“反饑餓、反內戰”學生游行的口號,然而它的回音卻是雨花臺下的槍聲。①在種種煩囂混雜的時代聲響的交織之下,少年張弦敏感的心緒飽受影響與折磨:“深深的苦悶和悲愴,過早地壓抑著我的少年的心。”這種刺激迫使了少年張弦努力尋求一些可堪寄托的愛好,或至少是能夠將他的注意力暫時從不堪的世相中稍微轉移到別處的事物。這時他發現讀書和寫作或許能借以遣懷。文學于是成了“*初的啟示和召喚”,似乎也隱然暗示了在以后的人生歲月中,張弦看待和描述世界的方式并非直接的回應,而總是略有緩沖曲折,以更為柔軟的形式而出之。大概是早年所經歷的憂患與困苦,使得他養成了某種與人世紛繁保持一定距離,悄悄躲在一隅,進行個人觀察的習慣。這樣的習慣不無逃避的意味,卻也提供了某種冷眼靜觀的可能。在張弦的觀察與記錄之中亦不乏飽滿充沛的浪漫詩情,這也就將往昔的苦難有所沖淡,且不無苦中作樂的積極意味。對過去的翻新、檢視和重識,也表現了一個人超越現實、克服艱困的不凡能力。當終有笑對苦難的那一日到來的時候,從前的憂傷都不算什么了,因它們都是可以被滌凈、沖刷并帶走的。 ……
- >
回憶愛瑪儂
- >
【精裝繪本】畫給孩子的中國神話
- >
羅庸西南聯大授課錄
- >
隨園食單
- >
月亮與六便士
- >
經典常談
- >
名家帶你讀魯迅:朝花夕拾
- >
煙與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