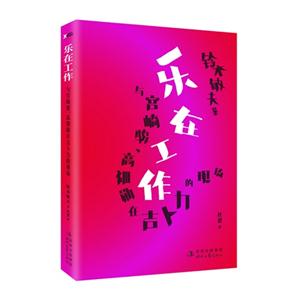-
>
東洋鏡:京華舊影
-
>
東洋鏡:嵩山少林寺舊影
-
>
東洋鏡:晚清雜觀
-
>
關中木雕
-
>
國博日歷2024年禮盒版
-
>
中國書法一本通
-
>
中國美術8000年
樂在工作-與宮崎駿.高畑勛在吉卜力的現場 版權信息
- ISBN:9787538740240
- 條形碼:9787538740240 ; 978-7-5387-4024-0
- 裝幀:簡裝本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樂在工作-與宮崎駿.高畑勛在吉卜力的現場 本書特色
1、首部由宮崎駿身邊的人撰寫宮崎駿的書,宮崎駿*親密的工作伙伴、吉卜力工作室制作人鈴木敏夫親自講述與宮崎駿、高畑勛之間的合作與互動關系。 2、動畫背后的故事。《千與千尋》的創作靈感來自夜總會?《哈爾的移動城堡》的建筑原型竟然在北歐?《龍貓》里的公共汽車差點被宮崎駿剪掉?目前為止對宮崎駿電影*權威的講述! 3、如何成為一個電影制作人。這是作者原本的內容主旨。也是本書在日本已有的讀者評論中經常被提及的點。
樂在工作-與宮崎駿.高畑勛在吉卜力的現場 內容簡介
鈴木敏夫,這位曾參與制作幾乎所有宮崎駿電影的知名動畫制作人,是如何踏入動畫這一行? 又是如何成為宮崎駿、吉卜力工作室不可或缺的得力伙伴?
《樂在工作(與宮崎駿高畑勛在吉卜力的現場)》由鈴木敏夫親述他進入日本德間書店后,因為負責《animage》動畫雜志創刊的編輯工作而得以認識宮崎駿、高畑勛等動漫畫家,進而參與動畫電影制作的過程。書中詳細敘述他與宮崎駿、高畑勛之間的各種互動,以及宮崎駿偉大作品背后所發生的故事。借此除了可以知道吉卜力工作室制作動畫時的狀況,更可一窺宮崎駿不為人知的一面,并進一步了解動畫大師的創作想法。
樂在工作-與宮崎駿.高畑勛在吉卜力的現場樂在工作-與宮崎駿.高畑勛在吉卜力的現場 前言
序——那些潛伏的記憶
我至今似乎從沒想過要去回憶整理自己所做過的工作,因為我總覺得無論如何回憶或整理,都會因為記憶本身脫離了事情發生時的情境,而與事實發生偏離。
因此,我從不打算記著自己做過的事,我甚至覺得有些事還是忘掉的好,從而我有時會努力去遺忘一些事情。清空自己才能更好地向前走,這似乎已經成為了指導我工作的原則。
這樣的想法又是源自何處?實際上我甚至連這個也想不起來了。或許是源自學生時代讀的宮澤賢治的書,又或許是源自寺山修司的影響吧。從他們那里,我獲得了我想要的東西,那就是過去的就讓它過去,我們都已經無能為力,眼前活生生的現在才是*重要的。
我和宮崎駿先生相識了近三十年。這些年我們幾乎天天都要談話,但是從不談過去的事,我們談的永遠都是現在。說的都是些現在必須去做的事,或者是有關未來一年的計劃。僅僅是這些,我們就有像山一樣說不完的話。
宮崎先生是出了名的健忘的人,不過我認為這正是他創作的秘密。對于一般人來說,有了像他這樣的成就,肯定會背著這些成就往前走,自己的創作手法肯定也只是在原有的基礎上不斷改進。但宮崎先生不是,他會像個新人導演一樣,去挑戰不同的創作方式。這是宮崎先生的創作風格。另一方面,這或許也是因為他總記不住自己做過的事吧。
我記得作家吉行淳之介……曾說過這樣的話: “被記憶遺忘了的事總歸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換句話,每個人的身體里都有刻骨銘心的記憶和被遺忘的記憶。對于那些不靠做筆記或是記日記就會遺忘的記憶,那就忘卻好了。吉行先生的原話我已經記不確切了,但正是這樣的不知什么時候潛伏在記憶里的東西才是*重要的,不是嗎?
身為制作人,做過什么樣的宣傳畫,在什么樣的條件下與別人進行合作,以及先例是如何等等,都非常重要。但是平時并不需要刻意去記得這些,只需在必要的時候去咨詢旁人即可,或者是去翻閱當時的材料,需要記起的東西自然會在腦海里浮現。
有工具就盡管利用起來,為此就需要作記錄,但記錄和記憶是完全兩樣的東西。我認為人的記憶容量有限,因此,要用有限的記憶去記更為重要的事情,而那些自己做過的事情則是*沒有必要記憶的。
我常常會在與人聊天的時候,用“我突然想起件事兒”這樣的話去擴大談話內容的范圍或是轉換話題。實際上,這是因為我的思維就是這樣。我常說著說著就想起某件事,或者別人的提問會突然讓我記憶的某部分復蘇。因為這些都是潛伏在身體里的記憶,這些并非刻意為之,而是不知何時,它們偷偷地潛伏進我記憶里。
正因如此,有的時候對于某件事是在哪兒發生的,當時有哪些人等等這些問題,我不一定會記得很確切,有時甚至連事件的前后順序也會搞混,但是我總認為重要的還是內容本身。比如說做計算題,55十44=99,2050+1030=3080,有時我們并不需要去記精確的數值.只需要對100或是3000這樣的大概數值有個了解就可以。
從月刊《動漫影像》(Animage)創刊開始,我接觸動漫世界也已經三十年了,吉卜力工作室成立至今也已二十周年。在這些年里,什么是我認為重要的記憶,又有哪些東西在不知不覺中潛伏進我記憶的深處?接下來我將原原本本地遵從我的記憶,把它們寫出來。
如果我說得太嘮叨或是敘述得太過天馬行空,還望見諒,因為“我突然想起來的事兒”實在是太多。我也不知道讀者是否會覺得這些事有趣或是否會從中得到啟發,我只是單純地希望讀者們能夠用自己的方式去閱讀本書。
后記
后記——誕生于閑聊中的作品
為什么我要出版這樣一本書呢?
我根據筆記上記載與巖波書店負責銷售的井上一夫先生的初次見面是在2005年12月16日,距離現在(2008)大概是兩年半以前的事了。
當時我們正在談有關電影《地海巫師》合作的事,他突然冒出一句:“要不您在巖波出本書吧?”
我馬上就拒絕了他。但是他那時還是給我留下了很特別的印象。理由之一是我聽說當他還在編輯部里工作時,是當時*暢銷作品《大往生》(永六輔,1994年)的主編。這令曾同為編輯的我記憶頗深。因為對于作為前編輯的我來說,對“*佳暢銷書”這樣的名頭還是很在意的。
我跟他聊了一會兒,心里就明白了,他是個善于抓住事物本質,而對那些無關緊要的小事又舍得放棄的人,看得出他在抓大局上做過相當充分的訓練。換句話,他是個非常善于把握分寸的人,但同時又具備觀察事物的細致性,而且他跟人交往的時候很注意照顧別人情緒,給人和藹可親的感覺,是個非常細心體貼的人,簡直可以說是個理想的編輯,再加上他和我同齡,我對他印象很深刻。
而且我記得,他在闡述自己想制作出版我所寫的書的動機時,竟然能夠把一些常人難以啟齒的理由笑嘻嘻地說出來:“我對高畑先生和宮崎先生都沒有興趣,但我對您非常感興趣。因為像高畑先生和宮崎先生那樣的天才,常人是無法復制他們的模式的,但如果是鈴木先生,常人還是可以模仿的。”
乍一聽真是大不敬的話,而他竟然能若無其事地說出來,真是服了他。不過,再轉念仔細想想,似乎我也常對初次見面的人這樣直言不諱,于是很自然地就記住了井上夏先生。
后來,高畑勛和宮崎駿的書都在巖波相繼出版發行,就是《漫畫電影的志向》和《布拉卡姆的的轟炸機》。在我看來,井上既然連不感興趣的兩個人的書都出了,可見是放棄勸我出書的事了,心中暗自得意,在此事上是我勝了他。
那以后,井上也沒有再來找過我。
后來有一天,為了慶祝《漫畫電影的志向》一書工作的完成,高畑先生和吉卜力出版部的田居因還有我三人去位于巖波書店附近的中國料理店吃飯。回來的路上,我們遇到了井上,他突然神秘地靠近我耳邊悄聲說道:“接下來就輪到鈴木先生你啦!”
我大吃了一驚,不知道說什么好。正如剛才所說的,我還以為出書的事已經結束了,沒想到井上并沒有忘記。就在我一時不知說什么好的情況下,不知怎的,就演變成我跟他約好下回詳談的局面了。
之后,高畑先生也靠過來對我說:“看來井上君的真命天子是你啊!”
當時是2007年的夏天,本書的寫作就這么開始了。
井上的方案是采取口述記錄的方式,他不僅要擔當采訪人還要自己執筆原稿。說真的,我還真有點懷疑,身為銷售負責人的他還要做這些事,能否忙得過來。他回答:“這些工作都留到下班后去完成。”沒想到他為此竟然要承受如此大的工作量。采訪時在場的還有古川義子,她負責記錄采訪的過程和整理采訪內容。吉卜力方面,則是由在《動漫影像》時期曾與我共事過的田居君參加。
我的助手白木伸子則是負責收集我曾寫過的文章和雜志上刊登過的對我的訪談,并提供給井上。
采訪一共進行了好多回,事情很順利地往前推進著,但我突然有種不好的感覺。以往我擔任過編輯,而現在是制作人,但在這件事上,我作為被采訪者,有種“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的感覺,壓力還是很大的。
不久,我有了一個緩解壓力的好機會。
那年10月,在經濟產業部主辦的日本國際電影節上,有一個環節叫“三小時劇場秀”,我收到了邀請函。它的主題是在三小時里可以選擇你自己喜歡或愿意表演的節目去表演。
如果是在一般場合我肯定會拒絕,但這次比較不一樣,傳話給我的人是前段時間我剛麻煩過他的重延浩先生,而且據他說,是日本電視臺的氏家齊一郎向主辦方推薦我的。
經過考慮,我萌生了一個主意:不如就把關于這本書的采訪現場搬到節目中去吧!也就是讓井上在節目中表演。
我暗暗地覺得這真是個一石四鳥的好主意,這樣一來我對主辦方也有了交代,書的內容也有了,而且還能反過來把井上變成砧板上的魚肉,這樣我的壓力自然也會消減。
雖然我的如意算盤是這樣打的,但井上是個跌倒也不會空手而回的人。
后來事情的發展果然沒依我所想。井上為此做了很多準備,包括整理了之前做過的采訪內容,我卻什么都沒有準備,而且事前對井上要提的問題也一無所知。結果當然可想而知:我再度成了砧板上的魚肉。
會后,我們參加了重延先生舉辦的宴會。在宴會上,我從井上那里聽到了這樣有趣的一段話:
“我認為把英語中的Editor翻譯成日語的編輯是不正確的。因為歐美的Editor是指編輯文字的人,而在日本,大多數情況下編輯并不只是干這樣的活。”
這話讓我印象深刻,我腦海里浮現出了井上所說的日本編輯的形象。一般來說,日本的編輯大多都要與作者閑聊,作品多半誕生于這樣的閑聊過程中。而歐美的Editor則是從作品的主題開始與作者交涉,這與日本的編輯完全不同,我覺得井上應該是對日本編輯的做法感到很驕傲。這樣想著想著,我想我明白了他要制作這本書的意圖。
我想起他曾對我說過:“我對您說的自己是個編輯型制作人感到很有興趣。”我很贊同他的觀點。
在日本,制作人的含義也與歐美有很大不同。在歐美國家,電影大多是以制作人的意思為主導來創作的,而電影導演不過是受雇于制作人罷了。而在日本,電影的主題大多是在制作人和導演的閑聊之中產生的,并以導演為中心來展開制作。
NHK的《專業人士的作風》欄目中,做到采訪我的那一段時,宮崎駿先生曾這樣評價我:“他總是不露痕跡地讓你去做事,不露痕跡地催促你做事的進度。”
*后我終于下定決心把書的事都拜托給了井上。
樂在工作-與宮崎駿.高畑勛在吉卜力的現場 目錄
一 “工作上公私不分/拜托的話就全權拜托”
——“動漫影像》創刊時期
二 “既然認識了,就希望能夠學到他們的素養”
——我與高畑勛及宮崎駿的相識
三 “*重要的是成為導演的伙伴”
——由《風之谷》發端的吉卜力工作室
四 “方圓三米以內到處是故事題材”
——宮崎駿的電影創作方法
五 “動畫制作就是大家一起從斜坡上往下滑”
——高畑勛的理論與實踐
六 “人就是背負著沉重的行囊向前走的”
——德間康快的生存之道
七 “小公司才能制作出好作品”
——“小工廠”吉卜力
引用文獻一覽表
鈴木敏夫履歷后記——誕生于閑聊中的作品
樂在工作-與宮崎駿.高畑勛在吉卜力的現場 節選
靈感從細節中采
制作電影時,宮崎駿的靈感總是從細節展開。人物要穿什么衣服?梳什么樣的頭發?吃什么食物?住在什么樣的房子里?故事情節都是從這些細節里豐滿起來的。
我曾寫過一篇文章,叫作《漫畫電影與動畫電影》(2004年)。現在我自然也會想到宮崎先生的電影制作方法。
把一個人的想法傳達給大眾,這就是日本的長篇漫畫電影的*大特征。并且它們都會非常強調細節,或者換句話說,這些作品通常都是從具體的細節開始去發展故事情節。比如,在作品的主線還沒完成前,在劇本沒有完成前,先把主人公的衣服設計、女主角的發型、他們所處的世界都先描繪出來,之后這些描繪與劇本之間就會產生互相影響。也就是說,故事的主題其實是在創作過程中才被發掘出來的。所以在日本,即便劇作家把故事的劇本先寫出來,也不能成為劇情的主導。
宮崎先生常會突然問我:“鈴木君,這次的女主角是個什么樣的人呢?”每當他這樣問我,我知道他其實是想問女主角到底該梳什么樣的發型。到底是梳小辮還是剪娃娃頭,還是留長發呢?但是連故事情節都還不確定就要幫女主角選擇發型,真是令人傷腦筋。但對于宮崎先生來說,這確是非常重要的事,他甚至會為此陷入沉思。到后來,我才發現原來女主角的發型存故事里被賦予了深層的含義。
源自記憶的原創建筑模型
很特別的一點是,當他創作動畫里的建筑時,他不去查閱任何資料。只是以迄今為止所掌握的知識和腦海中的印象為基礎,憑記憶去描繪出原創的建筑。比如《幽靈公主》中的達達拉的建筑、《神隱少女千與千尋》中的澡堂、《哈爾的移動城堡》中的城堡等,這些建筑的新穎設計都廣受好評。但其實這些建筑也都是源自于記憶的原創。對于他來說,重要的不是記錄而是記憶。我記得曾經有過那么一段往事,已經是大概20年前(1988年)的事了吧。宮崎先生和我們一行幾個人一起去芬蘭的阿蘭島。阿蘭島位于愛爾蘭的西邊的盡頭,以阿蘭編織風格的毛衣聞名,這里的人口只有800左右,因而沒有任何公共交通設施。那是發生在某天晚上的事,我們一行去了酒吧,在回來的路上,走著走著,視野里出現了我們居住的民房。雖然當時已經是夜里10點了,但在6月的芬蘭,天空依然很亮。那棟我們原本認為沒有什么特別之處的房子,此刻看著卻散發出異樣的光彩。
樂在工作-與宮崎駿.高畑勛在吉卜力的現場 作者簡介
鈴木敏夫,極其成功的制作人、漫畫家。1948年生,早期于德間書店的《Animage》上擔任總編,期間出席了《風之谷》的首映。1989年加入吉卜力,擔任過《魔女宅急便》、《幽靈公主》、《千與千尋》等數部宮崎駿的制作人。現在是吉卜力執行董事。
- 主題:喜歡宮崎駿動畫的不要錯過
第一次看這種幕后的書,喜歡宮崎駿的動畫很多年,這本書可以了解一些幕后創作的故事,很有趣。唯一不足的是,雖然書拿到手的時候是有塑封的,外觀也很新,但是內頁部分有一面全是黑黑的手指印,像是油墨的弄不掉。
- >
企鵝口袋書系列·偉大的思想20:論自然選擇(英漢雙語)
- >
我與地壇
- >
唐代進士錄
- >
煙與鏡
- >
姑媽的寶刀
- >
人文閱讀與收藏·良友文學叢書:一天的工作
- >
中國人在烏蘇里邊疆區:歷史與人類學概述
- >
名家帶你讀魯迅:故事新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