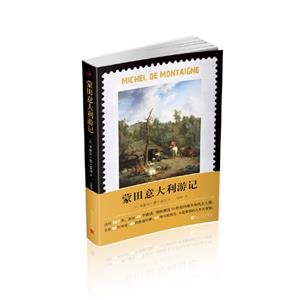-
>
貨幣大歷史:金融霸權與大國興衰六百年
-
>
(精)方力鈞作品圖錄
-
>
《藏書報》2021合訂本
-
>
(精)中國當代書畫名家作品集·范碩:書法卷+繪畫卷(全2卷)
-
>
(噴繪樓閣版)女主臨朝:武則天的權力之路
-
>
書里掉出來一只狼+狼的故事-全2冊
-
>
奇思妙想創意玩具書(精裝4冊)
蒙田意大利游記(八品-九品) 版權信息
- ISBN:9787020133574
- 條形碼:9787020133574 ; 978-7-02-013357-4
- 裝幀:平裝-膠訂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蒙田意大利游記(八品-九品) 本書特色
歷時527天,途徑42個城鎮,細致展現16世紀的意大利風土人情。
另附39封書信、39則家庭紀事、57句書房格言,盡顯蒙田的人生大智慧。
蒙田意大利游記(八品-九品) 內容簡介
在宗教戰亂之際開啟文化朝圣之旅,在漫游、遐想、探索中找尋自由的真諦。
蒙田于一五八〇年九月五日從法國博蒙出發,途經瑞士和德國,進行了為期十七個月又八天的意大利之旅。離開蒙田城堡的書房,他有機會深入不同的城邦和地區,事無巨細地記錄下所經之地的風土人情和當地人的宗教信仰,集結成《意大利游記》。與其他旅客關注點在名勝古跡上面不同,蒙田將目光停留在表現“人”的標志上,不論是鄉野播種的土地,還是城市的行政結構、馬路鋪設、建筑特點,還有新出現的工藝技術與農耕器械,他都表現出強烈的興趣,并不厭其煩地一一作一番認真的描述。蒙田旅行,就像蒙田寫作,信馬由韁,不僅欣賞到了自然界各種形態生生不息的演變,還了解到了五花八門的人生、觀念和風俗。
蒙田意大利游記(八品-九品)蒙田意大利游記(八品-九品) 前言
譯序 蒙田的《意大利游記》
馬振騁
當年,蒙田(一五三三— 一五九二)在《隨筆集》[1]第三卷提到,他獲得羅馬元老院和平民會議頒發的“羅馬公民證書”,人們才知道他旅行到過瑞士、德國和意大利。他對人性世情觀察入微,在《隨筆集》中記錄了很多家長里短的生活瑣事,然而對這次歷時一年多的漫游卻只字不提,未免讓人感到意外。歲月荏苒,這件事慢慢也被人淡忘了。
(一)
這樣過了近一百八十年。一七七〇年,尚斯拉德的教堂司鐸普呂尼神父搜尋佩里戈爾地區的歷史資料,來到了蒙田城堡,那時產業已經易主,由塞居爾·德·拉·羅凱特伯爵居住。管家給神父捧出一只舊箱子,里面都是遺忘了幾輩子的泛黃紙張。神父發現其中一份書稿,疑是蒙田寫的旅行日記。征得伯爵同意,他把稿子帶走再作深入研究。
神父對這份遺稿的真實性深信不疑后,再到巴黎請教幾位專家,他們一致認定這部旅行日記確是蒙田的手跡無疑。
稿子是小對開本,共二百七十八頁,十六世紀末的字體與紙張。手稿前面三分之一出自別人之手,三分之二是蒙田親筆。蒙田在意大利盧卡水療時,覺得用當地語言記事更加方便貼切,他書寫的部分中一大半用的是意大利語,回到法國境內又改用法語書寫。因而這是一部頗為奇特的作品。
若要讓這么一部文稿出版,要做大量的校勘編輯工作。首先要把上面隨意或者當時尚未定型的拼法辨別清楚,將幾乎不存在的標點補全,這工作由普呂尼神父開始做了,不久塞居爾伯爵收回稿子,交給更有名望的學者、國王圖書館館長默尼埃·德·蓋隆編輯出版。工作人員經過反復研討,后定下這條原則,原書只改動錯別字,詞匯與結構基本保持不變,即使有點欠通而又沒有把握勘正之處,為了不讓讀者懷疑對原作有絲毫的不尊重,也盡量保存原貌。
原稿中難處理的還是意大利語部分。首先意大利書面語言還處在蛻變時期,而蒙田使用——用蓋隆的話說——自以為是的那種意大利語,夾了許多托卡斯納地區的方言、俗語,這讓兩世紀以后的意大利人感到無從下手。幸而,付梓之前,撒丁國王御前考古學家、法國皇家碑銘古文藝學院外籍院士巴爾托利恰巧在巴黎,他欣然接受這項翻譯工作,還增加了一些語法與歷史注釋。一七七四年,蓋隆在羅馬和巴黎接連出版了三個版本,稍后在當年和第二年又出了兩個版本,可見當時此書受歡迎的程度。后來,存放在國王圖書館的日記原稿不翼而飛。蓋隆主編的五個版本雖有不少欠缺之處,相互還不完全相同,但是后來的人只能用這五個版本進行比對了。
(二)
原稿到編者手里時并不完整,缺了前面幾頁,據蓋隆說:“好像是撕去的。”缺了這幾頁,也少了一些重要信息。蒙田“投入智慧女神的懷抱”后十年,還在專心寫他的隨筆,在波爾多出版了一部分,絲毫沒有封筆的想法,怎么突然決定離開妻女,撂下莊園管理外出旅行,而且一走就是十七個月?
《隨筆集》對這次旅行沒有直接記載。蒙田只是說:“旅行我覺得還是一種有益的鍛煉,見到陌生新奇的事物,心靈會處于不停的活躍狀態。我常說培養一個人,要向他持之以恒地介紹其他五花八門的人生、觀念和風俗,讓他欣賞自然界各種形態生生不息的演變,我不知道除此以外還有什么更好的學校。”
在另一處又說:“貪戀新奇的脾性養成我愛好旅行的愿望,但是也要有其他情景促成此事。”
那么是什么情景促成了他的旅行呢?他在路上積極前往有溫泉浴場的地區,住上一段時間,醫治他從三四年前開始時時發作的腎絞痛。這是一個家族遺傳病,他的父親就是死于此病。因此有人說是這件事使他不敢掉以輕心,要走出城堡換一換空氣,試一試各地溫泉的療效。
缺了那幾頁,我們也不知道蒙田在什么情況下決定和準備出行的。這也只能從歷史與傳記中去拼合當時的情景。
一五八〇年,宗教戰爭在歐洲打得不可開交。法國歷史上稱為“三亨利之戰”也在這時候爆發。亨利三世代表王室勢力,亨利·德·那瓦爾支持被稱為“胡格諾”的新教派,亨利·德·吉茲不滿王室對新教的妥協態度,率領天主教神圣聯盟,是胡格諾的死敵。
從蒙田年表來看,蒙田在一五八〇年六月二十二日離開蒙田城堡。亨利三世已在一周前下令圍困被神圣聯盟占領的費爾。那是一座小城,但在宗教戰爭中是多次易手的兵家必爭之地。擁護王室的馬蒂尼翁元帥在七月七日實施圍城計劃。蒙田把戰爭看成“人類的一種疾病”,還是要履行貴族的義務。他未必參加沖鋒陷陣,不過七月份大部分時間是在費爾的外圍地區度過的。八月二日,他的好友菲利貝爾·德·格拉蒙伯爵陣前受傷四天后去世,蒙苗護送格拉蒙的靈柩到蘇瓦松。以后一個月他的行蹤就沒有記錄了。費爾攻城戰在九月十二日成功結束。《意大利游記》一開始提到蒙田是九月五日,說他已在巴黎北面瓦茲河上的博蒙啟程了,“……蒙田先生派馬特科隆先生隨同那位青年侍從,火速前去探望那位伯爵,看到他受的傷還不致有生命之 虞。”
那位受傷的伯爵是誰?是不是在圍城中受傷的?都不清楚。我們讀了后面的文章才知道,同行旅伴只是四個不滿二十歲的青年,包括他的親弟弟馬特科隆領主。旅伴中好像就只有一人陪同他走完全程。此外就是他們的隨從仆人。
(三)
意大利旅行日記的一個特殊之處,就是前面三分之一由另一人代寫,由于他的介入,我們在閱讀這部書時就多了一個維度。
這個人是誰?不知道;是什么身份?不知道。他在旅途中照顧行李、安排行程、聯系食宿,對蒙田的生活起居真情關切,此外還執筆撰寫沿途見聞。從他的語言與字跡來看,他肯定不是一個沒有文化的下人,更可能是一位不得志的文人。因而姑且稱他為“秘書”。他在日記中提到蒙田時,用第三人稱“蒙田先生”,可是他的文風與蒙田頗為相像,因此后人認為他是在蒙田口授下寫的。但是從事情的提法來看又不像,顯然“秘書”處理情節有相當的自主權。
旅途中他并不始終陪伴在蒙田身邊,有時他到前站辦理其他事項,然而他不在時蒙田的行程照樣記在日記里。是事后聽蒙田敘述補寫上去還是怎么的?但是層次不亂,完全可以分清哪些話應該派在蒙田頭上,還是秘書頭上。在他寫的那部分,“我認為”“以我看來”,只是指秘書本人;“他們”指“蒙田先生等人”,“我們”指“蒙田他們和自己”,偶爾“我們”與“他們”交替使用,這確實是一種奇異的文體。
秘書以旁觀者的身份實錄旅途情境,不論如何客觀,總摻雜個人感情,因而在他的筆端下,我們看到的不是在書房對著白紙說話的蒙田,而是在生活中對著人說話的蒙田。這部分就成了珍貴的蒙田畫像與自畫像。這對蒙田其人其事,反而有更多的記述,也帶來更多的想法,無意中也包含更多的暗示。蒙田旅行日記詳盡的編注者福斯達·加拉維尼在一篇序言中說:“日記若一開始就由蒙田自己來寫,我們對他的旅行、對他的旅行方式,總之對蒙田本人反而更少知道。”
(四)
蒙田,這個習慣于在書本中漫游、遐想、探索的人,一旦走出塔樓里的圓形書房,要看的是什么呢?
他有機會深入不同的國家,并抓住機會去了解當地人。一般游客都會說上一大通的名勝古跡,不是他的重點關注對象。他的目光停留在表現“人”的標志上,不論是鄉野播種的土地,還是城市的行政結構、馬路鋪設、建筑特點,以及新出現的工藝技術與農耕器械,都表現出強烈的興趣。他對新奇的虹吸現象、城門防盜機關,也努力作一番認真的描述。
他饒有興趣地觀看江洋大盜卡泰納的伏法場面、猶太會堂里的割禮儀式、禮拜堂內裝神弄鬼的驅魔作法、賽神會上鞭笞派慘不忍睹的自虐;記述自己晉謁教皇的儀禮,出席貴族家的宴請、圣周期間羅馬萬人空巷的宗教大游行。蒙田讀過許多古希臘羅馬的書籍,驚異于古代名妓的華麗生活;如今到了羅馬,也要領略一下這些名媛的遺風流韻。據他說在羅馬、威尼斯只是想與青樓女子聊一聊她們的偏門子生活,然而陪聊費與度夜資同價不打折,這令老先生像挨了斬,感覺很不爽。
蒙田到了一個地方,不像其他法國人喜歡扎堆。他遠遠避開老鄉,怕有人用法語上來搭訕,進餐廳坐到外國人多的桌子邊,點的也是當地的特色菜。他入境隨俗,充分享受當地人的舒逸生活,組織舞會邀請村民參加,做游戲,搞發獎,時而還跟村姑說幾句俏皮話調調情,充分發揚中世紀鄉紳好客的風氣。
盡管歷代有人對蒙田的宗教觀爭論不休,他毫不諱言自己是天主教徒。但是他心底所謂的神性其實只是崇高的人性。他引用圣奧古斯丁的話說,人自以為想象出了上帝,其實想象出來的還是人自己。宗教只是以其包含的人性,以其在人的心靈與生活中所占的地位來說,才使他關切。新舊兩大教派大打出手,他覺得都是在假借神的旨意做違反神的事。他對宗教戰爭深惡痛絕,他路上遇到新教中的人,不論是路德派、加爾文派,還是茨溫利派,都主動接近他們,努力了解他們推出改革的真意。這種做法需要極大的勇氣與寬容,因為那是個不同教派的人都可以任意相互誅殺的時代。對他來說,跟教士談論改革與跟妓女了解生活,都是重要性不相上下的人性研究與自我教育。
(五)
蒙田旅行,就像蒙田寫作,表面上信馬由韁。他的隨筆從古代軼事,摻入個人議論,引到生死、苦樂、人生須臾、命運無常的命題,后告示世人怎樣過好這一生。蒙田走在旅途上,一路雖有日程表,但是隨時可以改變,好像也是走到哪里是哪里。有評論家說,要不是波爾多議會正式函告他已當選為波爾多市長,又加上國王敦促他屆時上任,真還不知道他什么時候會打道回府呢。
那么,這趟不知其如何開始、原本也可能不知其如何結束的旅行,到底是為的什么?既然已無法從其主觀意圖去了解,不妨從事實過程上去揣測和分析。
一五八〇年九月五日從法國博蒙出發,途經瑞士、奧地利和德國的意大利之旅,歷時共十七個月又八天。從一五八〇年十月二十八日進入意大利博爾薩諾之日起,到一五八一年十月三十一日離開都靈和蘇斯之日止,在意大利整整過了一年又四天。旅居意大利時,又兩次進入羅馬。次從一五八〇年十一月三十日到一五八一年四月十九日,逗留四個半月,然后離開到外省旅行。第二次從一五八一年十月一日到十月十五日,又盤桓半個月。之前,四月五日獲得正式羅馬公民資格證書。他進入羅馬時是旅客,離開羅馬時是公民。一直自稱不慕名利的蒙田在《隨筆集》里全文轉錄證書的內容,可見他的自尊心感到極大的滿足。
文藝復興是古希臘文明的復活,人文主義要讓一切歸于以人為本,中世紀一統天下的神學史觀從此開始走向沒落。在歐洲首先舉起文藝復興火炬的是意大利。
那時亞平寧半島上各城邦公侯都稱雄一方,為了建立自己的霸業與威望,競相網羅人才,獎勵文學藝術、知識科學。這大概也是在積累今日所謂的軟實力,在東西方歷史上早已不乏其例。
當時歐洲人到意大利旅行,接近于一種朝圣行為。在蒙田內心還有更深切的沖動與理由。我們知道,蒙田還在牙牙學語時,父親從意大利帶回來一位不會說法語的德國教師,讓三歲的蒙田跟著他學習拉丁語,開始羅馬文化培養。蒙田說自己知道盧浮宮以前就知道朱庇特神殿,知道塞納河以前就知道臺伯河。他更可以算是個羅馬人。
他初到羅馬,雇了一名導游,后來把他辭了。前一個晚上靜心在燈下閱讀不同的圖片和書籍,第二天游現場去印證自己的書本知識。普通游客看到的羅馬只是它頭上的一片天空和腳下的地理位置。蒙田對羅馬的認識更多是抽象與靜觀的。他說:“我覺得自己對這個世紀一無用處,也就投身到那個世紀,那么迷戀這個古老的羅馬,自由、正直、興隆昌盛……叫我興奮,叫我熱情澎湃。因此我永遠看不夠羅馬人的街道與房屋,以及羅馬直至對蹠地的遺址廢墟,每次都興意盎然。看到這些古跡,知道曾是那些常聽人提起的歷史名人生活起居的地方,使我們感動不已,要超過聽說他們的事跡和閱讀他們的記述……”
歷史就是這樣殘酷無情,羅馬擴張它的疆域和文明,同時也使多少生靈涂炭,多少民族淪為奴隸;它征服全世界,全世界也對它恨之入骨。羅馬消亡了,它的廢墟也被埋葬,要做到它湮滅無聞。
然而那么多世紀過去,那么多浩劫降臨,羅馬的廢墟還是保存了下來,還從那里掀起了文藝復興運動,使歐洲文明得以延續并發揚光大。這座普天下萬眾景仰的永恒之城……“天下還沒有一個地方受到天庭這么堅定不移的厚愛,即使廢墟也輝煌燦爛,它在墳墓里也保持帝國皇家的氣派。”蒙田到意大利的旅行,我們不是可以說是對古希臘羅馬文化的一次朝拜,為他的寫作增添更為深刻的論述?
(六)
《意大利游記》在我國還是初次翻譯。今天能從這部書里看到什么呢?首先是它直接反映了十六世紀的意大利。一五二七年,羅馬遭到了神圣羅馬帝國查理五世軍隊的洗劫,那時還處于百廢待興的階段,雖然達·芬奇、米開朗琪羅、拉斐爾、提香、丁托列托、維羅納斯、柯雷喬已經完成了自己的杰作。但是真正用繪畫、雕塑等藝術品把羅馬、佛羅倫薩、威尼斯裝扮得玲瓏剔透、光彩炫目的,還是在此后不久的西克斯特五世教皇時代。蒙田看到的主要是希臘精神的傳承與新舊羅馬的交接,這點與二百多年后歌德的游記頗不相同。歌德看到的是文藝復興后結出的果,蒙田看到的是文藝復興前留下的根。
沿途城鎮在蒙田看來不是孤立的單體,而是珍珠似的串在一起的長鏈,在時間上如此,在空間上也是如此。經過一個地方都鄭重其事標出距離,如:
洛雷托(十五 里)……
……
安科納(十五里)……
那就是說洛雷托離前一站十五里,而安科納又離洛雷托十五里。這個標志想來蒙田也有他的用意,當年馬可·波羅行走在路上得到這樣的體會,他說:“旅行時你意識到差別在消失,每座城市與所有城市都是相像的。”但是蒙田又像司湯達所說的,一路上眼睛看著不同的東西。距離是間隔符號,也是連接符號。
《意大利游記》還向我們證實,蒙田在《隨筆集》中對自己的描述是真誠的,首先這部書是寫給自己看的,生活中的真性情與語言上的不講究畢露無遺。旅行日記寫于去瑞士、德國和意大利的來回路途上。此后在波爾多當了兩任市長,共四年;一五八五年卸職后,在蒙田城堡書房閱讀大量歷史書籍,繼續寫他的隨筆。他若有意要出版日記,完全有時間整理修飾。現在這樣出版,雖然有違于作者的原意,倒反留下一件可信的證據。有人說《意大利游記》是《隨筆集》的后店,意思是店堂賣的與庫房藏的貨色沒有什么兩樣。不是像盧梭在《懺悔錄》中說的:“我把蒙田看作這類假老實的帶頭人物,他們講真話也為的是騙人……只暴露一些可愛的缺點……蒙田把自己畫得更酷似本人,但是只畫了個側面。”《意大利游記》給我們提供了另一個側面,這兩個側面是完全對得上號的。
這部作品文采不追求飛揚華麗,真情則相當流露。從閱讀的角度來看,也有一些不甚有趣的章節。我們在隨筆中看到蒙田,如同在他逝世后三十年出生的莫里哀,對當時的醫生極盡嘲笑之能事。蒙田不信任醫生,說后悔以前沒有對自己病程的詳細記錄,以便總結出對自己的治療方法。他到溫泉浴場,不厭其煩地談一天喝下多少杯礦泉水,泡上多長時間溫泉,尿出什么樣大小形狀的結石等等。這有點令人掃興,但也不能怪他,還是前面那句話,他沒有要別人讀他這部書,就像外人擅自推開你的房門,可不能怪你怎么赤裸上身站在鏡子前不夠雅觀。
蒙田《隨筆集》出版前后都作過幾次重大增刪修改。此書若由蒙田親自定稿,肯定不會像目前這樣,如今這部保持原生態的率性之作,讀者看來也有其自然嫵媚之處。
蒙田意大利游記(八品-九品) 目錄
蒙田意大利游記(八品-九品) 相關資料
穿越法國去瑞士
(一五八〇年九月五日—十八日) 這部分日記由秘書用法語寫成[1]……蒙田先生派馬特科隆先生隨同那位青年侍從,火速前去探望那位伯爵,看到他受的傷還不致有性命之虞。在博蒙,埃斯蒂薩克先生加入隊伍同路旅行,跟著他一起來的有一位貴族、一名貼身男仆、一頭騾子,還有兩名跟班和一名趕騾夫隨同步行,他分攤一半路資。一五八○年九月五日星期一,午飯后我們從博蒙出發,馬不停蹄到了
莫城(十二里)吃晚飯,這是一座美麗的小城鎮,坐落在馬恩河畔。小城分三部分。市區與郊區在河的這邊,朝向巴黎。過了橋另有一塊地方稱為市場,河水環繞,四周還有一條風光旖旎的溝渠,那里有大量居民和房屋。這地方從前筑有巍峨的城墻和敵樓,防衛森嚴;然而在第二次胡格諾動亂中[2],因為大多數居民屬于這一派,所有這些碉堡要塞都被下令拆毀。這個城區,雖然其余部分俱已淪陷[3],但仍堅持抵抗英國人的進攻;作為嘉獎,全城居民都免繳人頭稅和其他稅項。他們指出馬恩河上有一座長約兩三百步的小島,據說是英國人投放在水中的填土,在上面置放輜重武器以攻擊市場,因年深日久已成了實土。
在郊區,我們看到了圣法隆修道院,這是一座非常古老的寺院,他們給我們看丹麥人奧奇埃[4]的住屋和他的客廳。有一間古代膳房,放了一些大而長的石桌子,其體積實屬罕見。膳房中間在內戰以前涌出一泓清泉,供三餐之用。大部分修士還是來自貴族。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有一座顯赫的古墓,上面直躺著兩具騎士的石頭雕像,身軀巨大。他們說這是丹麥人奧奇埃和另一位輔弼大臣。上面既沒有字碑,也無族徽,只有一名本堂神父約在百年前命人添加的那句拉丁語句子:埋葬于此的是兩位無名英雄。他們給我們看的寶物中有這兩位騎士的遺骸。從肩胛到肘子的骨頭,約有我們當代普通身材者整條胳臂的長度,比蒙田先生的胳臂還稍長一點。他們還給我們看他們的兩把寶劍,長度大約相當于我們的雙手劍,劍鋒上有不少缺口。
在莫城時,蒙田先生前去拜訪圣司提反教堂的司庫朱斯特·特萊爾,在法國知識界頗有聲望,是一位年已六十的瘦小老人,曾游歷埃及和耶路撒冷,在君士坦丁堡住了七年。他給蒙田參觀他的圖書館和花園內的珍奇。罕見的是一棵黃楊樹,茂密的枝葉向四處展開,巧妙修剪后像一只渾圓光溜的球,有一個人那么高。星期二,我們在莫城吃過中飯后,趕到
夏爾里(七里)投宿。星期三中飯后前去
多爾芒(七里)投宿。第二天星期四上午,趕到
埃佩爾奈(五里)吃中飯。埃斯蒂薩克先生和蒙田先生到了那里,就去圣母寺望彌撒,這也是他們的習慣。還因為從前斯特羅齊元帥在蒂翁維爾圍城戰中戰死時,蒙田先生親眼目睹人家把他的尸體擔進這座教堂。他打聽他的墓地,發現他埋在那里,面對大祭臺既沒有墓碑也沒有族徽和墓志銘之類的標志。有人告知我們說是王后下令讓他下葬時不用任何儀式和排場,因為這是那位元帥的意愿。雷恩市主教是巴黎漢納金家族的人,那時是那座教堂的本堂神父,正在那里主持祭禮。那天也是九月圣母節的日子。
彌撒后,蒙田先生在教堂里跟馬爾多納先生交談,他是知名的耶穌會會士,精通神學與哲學。那時午飯后,馬爾多納先生到蒙田先生的住處來拜訪時,他們好多話都是在討論學問。他們還談到其他事,由于馬爾多納與內維爾先生去過列日,剛從那里的水療浴場回來,對蒙田先生說那里的水非常冷,大家認為飲用的水愈冷療效愈好。那里的水冷得有人喝了會打冷戰和起雞皮疙瘩;但是過不了一會兒胃里會感覺十分暖和。他每次喝上一百盎司。但有的人根據自己的需要用不同刻度的杯子。這水不但可以在空腹時喝,還可以在飯后喝。他說療效跟加斯科涅的礦泉相似。就他本人來說,他好幾次喝了之后全身出汗、心跳加快,感到其藥力很強,對身體卻沒有任何損害。他還看到試驗,把青蛙和其他小動物扔在水里便立即死亡。據說在盛了這種水的杯子上放一塊手帕,手帕立即就會發黃。飲用至少兩周或三周。那個地方生活食宿非常方便,適合腸梗阻與尿結石病的治療。然而,內維爾先生和他待了一陣后并不比以前更健康。
他身邊還跟著內維爾先生的管家,他們給蒙田先生一份帖子,上面提到蒙龐西埃先生與內維爾先生的糾葛緣由,為了讓他有所知曉,有貴族問起時可以代為解釋。我們在星期五上午離開,到了
沙隆(七里),投宿在王冠旅館,這是一家精致的旅舍,使用銀質餐具;大部分床單與蓋被是絲做的。這個地區的普通民房用切成小方塊的白堊土做成,約半尺左右寬,其他還有用干打壘的,同樣形狀。第二天我們在午飯后離開,投宿在維特里·勒·弗朗索瓦(七里),坐落在馬恩河畔的一座小城,三四十年前建立在另一個被燒毀的維特里的舊址上[1]。它保留了原有布局勻稱、風景宜人的特點,城中心有一座歸于法國美之列的正方形大廣場。
我們在這里聽到三則難忘的故事。一則是波旁家族的吉茲老公爵夫人,年已八十七歲,尚健在,還能步行四分之一里地。蒙田意大利游記(八品-九品) 作者簡介
米歇爾·德·蒙田(1533-1592),生于法國南部佩里戈爾地區的蒙田城堡。法國文藝復興后期重要的人文主義作家,啟蒙運動以前法國的知識權威和批評家,也是人類感情的冷峻的觀察家,一位對各民族文化,特別是西方文化進行冷靜研究的學者。蒙田出身貴族,早年學習拉丁文,成年后在相當長的時期內深居簡出,閉門讀書、思考。1572年開始撰寫被稱為“十六世紀各種知識的總匯”的《隨筆集》。
馬振騁,1934年生于上海,法語文學翻譯家,首屆“傅雷翻譯出版獎”得主。先后翻譯了圣埃克蘇佩里、波伏娃、高乃依、薩巴蒂埃、克洛德•西蒙、紀德、蒙田、杜拉斯、米蘭·昆德拉、洛朗•戈伐等法國重要文學家的作品。著有散文集《巴黎,人比香水神秘》《鏡子中的洛可可》《我眼中殘缺的法蘭西》《誤讀的浪漫:關于藝術家、書籍與巴黎》等。其《蒙田隨筆全集》(全三卷)2009年榮獲首屆“傅雷翻譯出版獎”,并被評為“2009年度十大好書”。
- >
二體千字文
- >
詩經-先民的歌唱
- >
李白與唐代文化
- >
隨園食單
- >
【精裝繪本】畫給孩子的中國神話
- >
朝聞道
- >
山海經
- >
月亮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