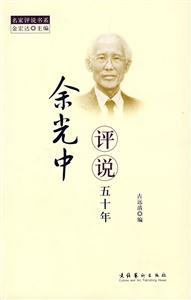-
>
百年孤獨(2025版)
-
>
易中天“品讀中國”系列(珍藏版全四冊)
-
>
心歸何處
-
>
(精裝)羅馬三巨頭
-
>
野菊花
-
>
梁啟超家書
-
>
我的父親母親:民國大家筆下的父母
余光中評說五十年 版權信息
- ISBN:9787503931727
- 條形碼:9787503931727 ; 978-7-5039-3172-7
- 裝幀:暫無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余光中評說五十年 內容簡介
本書主要包括:大家須浩瀚,視線內外的余光中,自述-煉石補天蔚晚霞,訪問,印象,漫議,爭鳴,論列等。
本書是名家評說叢書系列之一種,精選國內外諸多名家對余光中的各類評說文章,分為《訪談》、《印象》、《爭鳴》、《論列》等幾輯,博采史料,尋蹤研究歷程,兼具學術性與可讀性,具有較強的資料價值。
余光中評說五十年 目錄
大家須浩瀚
本書編者前言
視線內外的余光中
自述
煉石補天蔚晚霞
訪問
在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之間——余光中先生訪談錄
余光中:把島上的文字傳回中原
印象
爸,生日快樂
詩人素描
筆花飛舞——余光中湘行散記
鄉(xiāng)愁詩人返鄉(xiāng)說鄉(xiāng)愁
昔年我讀余光中
和余光中面對面
漫議
談余光中《舟子的悲歌》
詩壇祭酒余光中
說“三”道“四”
“奇異的光中”——《余光中詩歌選集》讀后感
正才之風
從余勇可賈到余音繞梁
“騙子”詩人和他的詩
關于余光中贊助李敖賣牛肉面的廣告詞
爭鳴
(一)評“鄉(xiāng)土文學”之爭
談“人性”與“鄉(xiāng)土”之類(節(jié)錄)
評臺北有關“鄉(xiāng)土文學”之爭
關于臺灣“鄉(xiāng)土文學”的論戰(zhàn)
《詩潮》與詩壇風云——洛夫與余光中在說些什么?
(二)評余光中的詩
評余光中的頹廢意識與色情主義
駁斥陳鼓應的余光中罪狀
余光中的詩傳播色情主義?
(三)向歷史自首
視線之外的余光中
視線之內的余光中
抑揚余光中
也談余光中《狼來了》之事件
“二余”問題與“死不認賬”
何必對余光中求全
向歷史自首?——溽暑答客四問
爭鳴:我對余光中事件的認識與立場
(四)評余群、余派
余派以外——一些回顧,一些感覺
流矣,派平!
“余派”
非余
余群、余派、沙田幫……——沙田文學略說
余光中·香港·沙田文學
沙田派簡論一兼答劉登翰先生
論列
璀璨的五彩筆——余光中作品概說
論余光中的《天狼星》
與余光中拔河
余光中的現(xiàn)代中國意識
繁華一季,盡得風騷——初論余光中的散文
隔海的繆斯:論臺灣詩人余光中的詩藝
“鐘整個大陸的愛在一只苦瓜”
余光中性愛詩略論
風景里的中國——余光中游記的一種讀法
附錄
余光中大事年表
余光中評說五十年 節(jié)選
自述
煉石補天蔚晚霞
余光中
一
五十年前,我的**本詩集《舟子的悲歌》在臺灣出版。半世紀來,我在臺灣與香港出版的詩集、散文集、評論集與譯書,加上詩選與文選,也恰為50本。若論創(chuàng)作時間,則我的**首詩《沙浮投海》還可以追溯到1948年。
但是晚到20世紀80年代初期,經過流沙河、李元洛的評介,大陸的讀者才開始看到我的作品。至于在大陸出書,則要等到80年代末期,由劉登翰、陳圣生選編,福建海峽文藝出版社出版的《余光中詩選》,在1988年*先問世。迄今十幾年間,我在各省市已經出書20多種,其中還包括套書,每套從3本到7本不等。
收入目前《余光中集》里的,共為18本詩集、10本散文集、6本評論集。除了13本譯書之外,我筆耕的收成,都在這里了。不過散文與評論的界限并不嚴格,因為我早年出書,每將散文與評論合在一起,形成文體錯亂,直到《分水嶺上》才抽刀斷水,涇渭分明。
早年我自稱“右手為詩,左手為文”,是以詩為正宗,文為副產,所以把**本散文集叫做《左手的繆斯》。其中的**篇散文《石城之行》寫于1958年。說明我的散文比詩起步要晚十年,但成熟的過程比詩要快,吸引的讀者比詩更多。至于評論,則在廈門大學的時候已經開始,雖是青澀的試筆,卻比寫抒情散文要早很多,比寫詩也不過才晚一年。
我是在1949年的夏天告別祖國大陸的。在甲板上當風回顧鼓浪嶼,那彷徨少年絕未想到,這一別幾乎就是半個世紀。當時我已經21歲,只覺得前途渺茫,絕不會想到冥冥之中,這不幸仍有其大幸:因為那時我如果更年輕,甚至只有十三四歲,則我對后土的感受就不夠深,對華夏文化的孺慕也不夠厚,來日的歐風美雨,尤其是美雨,勢必無力承受。
要做一位中國作家,在文學史的修養(yǎng)上必須對兩個傳統(tǒng)多少有些認識。詩經以來的古典文學是大傳統(tǒng),“五四”以來的新文學是小傳統(tǒng)。當年臨風眷顧的那少年,對這兩個傳統(tǒng)幸而都不陌生:古典之根已蟠蜿深心,任何外力都不能搖撼;新文學之花葉也已成蔭,令人流連。不過即使在當年,我已經看出,新文學名家雖多,成就仍有不足,詩的進展尤其有限,所以我有志參加耕耘。后來兼寫散文,又發(fā)現(xiàn)當代的散文頗多毛病,乃寫《剪掉散文的辮子》一文逐一指陳。
早在廈門大學時期,我已在當地的《江聲報》與《星光報》上發(fā)表了六七首詩,7篇評論,2篇譯文,更與當地的作家有過一場小小的論戰(zhàn)。所以我的文學生命其實成胎于大陸,而創(chuàng)作,起步于南京,刊稿,則發(fā)軔于廈門。等到四十年后這小小作者重新在大陸刊稿,競已是老作家了。一生之長亦如一日之短。早歲在大陸不能算朝霞,只能算熹微。現(xiàn)在由百花文藝出版社推出《余光中集》,倒真像晚霞滿天了。
除了在大陸的短暫熹微之外,我的創(chuàng)作可以分為臺灣、美國、香港三個時期。臺灣時期*長,又可分為臺北時期(1950年至1974年)與高雄時期(1985年迄今)。其間的十一年是香港時期(1974年至1985年)。至于先后五年的美國時期(1958年至1959年、1964年至1966年、1969年至1971年),則完全包含在臺北時期之中。
然而不論這許多作品是寫于臺灣、香港或美國,不論其文類是詩、散文或評論,也不論當時揮筆的作者是少年、壯年或晚年,21歲以前在那片華山夏水笑過哭過的日子,收驚喊魂似的,永遠在字里行間叫我的名字。在夢的彼端,記憶的上游,在潛意識蠢蠢的角落,小時候的種種切切,尤其是與母親貼體貼心的感覺,時歇時發(fā)地總在叫我,令浪子魂魄不安。我所以寫詩,是為自己的七魂六魄怯禳禱告。
到2000年為止,我一共發(fā)表了805首詩,短者數行,長者多逾百行。有不少首是組詩,例如《三生石》便是一組3首,《六把雨傘》與《山中暑意七品》便各為6首或7首;《墾丁十九首》則包羅得更多。反過來說,《戲李白》、《尋李白》、《念李白》雖分成3首,也不妨當作一組來看。他如《甘地之死》、《甘地朝海》、《甘地紡紗》,或是《星光夜》、《向日葵》、《荷蘭吊橋》也都是一題數詠。所以我詩作的總產量,合而觀之,不足八百,但分而觀之,當逾千篇。
論寫作的地區(qū),內地早期的青澀少作,收入《舟子的悲歌》的只得3首。三次旅美,得詩56首。香港時期,得詩186首。臺北時期,得詩348首。高雄時期,得詩212首。也就是說,在臺灣寫的詩一共有560首。如果加上在《高樓對海》以后所寫迄未成書之作,則在臺灣得詩之多,當為我詩作產量的十分之七。所以我當然是臺灣詩人。不過詩之于文化傳統(tǒng),正如旗之于風。我的詩雖然在臺灣飄起,但使它飄揚不斷的,是五千年吹拂的長風。風若不勁,旗怎能飄,我當然也是*廣義*高義的中國詩人。
自80年代開放以來,我的詩傳人祖國大陸,流行*廣的一首該是《鄉(xiāng)愁》,能背的人極多,轉載與引述的頻率極高。一顆小石子競激起如許波紋,當初怎么會料到?他如《民歌》、《鄉(xiāng)愁四韻》、《當找死時》幾首,讀者亦多,因此媒體甚至評論家干脆就叫我做“鄉(xiāng)恐詩人”。許多讀者自稱認識我的詩,都是從這一首開始。我卻恐怕,或許到這一首也就為止。
這綽號給了我鮮明的面貌,也成了將我簡化的限制。我的詩,主題歷經變化,鄉(xiāng)愁之作雖多,只是其中一個要項。就算我一首鄉(xiāng)愁詩也未寫過,其他的主題仍然可觀:親情、愛情、友情、自述、人物、詠物、即景、即事,每一項都有不少作品。例如親情一項,父母、妻女,甚至孫子、孫女都曾入詩,尤以母親、妻子詠歌*頻。又如人物,于今則有孫中山、蔡元培、林語堂、奧威爾、全斗煥、福特、薇特、赫本、楊麗萍;于古則有后羿、夸父、荊軻、昭君、李廣、史可法、林則徐、耶穌、甘地、勞倫斯。梵高前后寫了5首。詩人則寫了近20首,其中尤以李白5首、屈原4首*多。
我寫散文,把散文寫成美文,約莫比寫詩晚了十年。開始不過把它當成副業(yè),只能算是“詩余”。結果無心之柳競自成蔭,甚至有人更喜歡我的散文。后來我竟發(fā)現(xiàn),自己在散文藝術上的進境,后來居上,竟然超前了詩藝。到了《鬼雨》、《逍遙游》、《四月,在古戰(zhàn)場》諸作,我的散文已經成熟了;但詩藝的成熟卻還要等待兩三年,才抵達《在冷戰(zhàn)的年代》與稍后的《白玉苦瓜》二書的境界。
中國文學的傳統(tǒng)向有“詩文雙絕”的美談,證之《古文觀止》,諸如《歸去來辭》、《桃花源記》、《滕王閣序》、《阿房宮賦》、《秋聲賦》、《赤壁賦》等美文名著,往往都出自詩人之手。這些感性的散文,或寫景,或敘事,或抒情,都需要詩藝始能為功,絕非僅憑知性,或是通情達理就可以應付過去。
一開始我就注意到,散文的藝術在于調配知性與感性。知性應該包括知識與見解。知識屬于靜態(tài),是被動的。見解屬于動態(tài),見解動于內,是思考,表于外,是議論。議論要縱橫生動,就要有層次,有波瀾,有文采。散文的知性畢竟不同于論文,不宜長篇大論,尤其是直露的推理。散文的知性應任智慧自然洋溢,不容作者炫學矜博,若能運用形象思維,佐以鮮活的比喻,當更動人。
感性則指作品中呈現(xiàn)的感官經驗:如果能令讀者如臨其境,如歷其事,就可謂富于感性,有“臨場感”,也就是電影化了。一篇作品若能寫景出色,敘事生動,感情已經呼之欲出,只要再加點睛,便能因景生情,借事興感,達到抒情之功。
不過散文家也有偏才與通才之別,并非一切散文家都擅于捕捉感性。寫景,需要詩才。敘事,需要小說家的本領。而真要抒情的話,還得有一支詩人之筆。生活中體會到的感性若要奔赴筆端,散文家還得善于捕捉意象,安排音調。
一般散文作者都習于談論人情世故,稍高一些的也能抉出若干理趣、情趣,但是每到緊要關頭,卻無力把讀者帶進現(xiàn)場去親歷其境,只能將就搬些成語,敷衍過去。也就是說,一般散文作者都過不了感性這一關,無力吸收詩、小說、戲劇甚至電影的藝術,來開拓散文的世界,加強散文的活力。
所以當年我分出左手去攻散文,就有意為這歉收的文體打開感性的閘門,引進一個聲色并茂、古今相通、中西交感的世界。而要做到這一點,“五四”以來的中文,那種文言日疏、西化日親的白話文,就必須重加體驗,回爐再煉。所以在《逍遙游》的后記里我說:“在《逍遙游》、《鬼雨》一類的作品里,我倒當真想在中國文字的風火爐中,煉出一顆丹來。我嘗試在這一類作品里,把中國的文字壓縮、捶扁、拉長、磨利,把它拆開又拼攏,折來且疊去,為了試驗它的速度、密度和彈性。我的理想是要讓中國的文字,在變化各殊的句法中交響成一個大樂隊,而作家的筆應該一揮百應,如交響樂的指揮杖。”
當年的我野心勃勃,不甘在散文上追隨“五四”的余韻,自限于小品與雜文。我的詩筆有意越過界來,發(fā)展大品與美文,把散文淬煉成重工業(yè)。在倉頡的大熔爐里,我有意把文言與西語融進白話文里,鑄造成新的合金。
尤其是到了60年代中葉,一來因為我青春正盛,萬物有情;二來因為初在美國馳車,天迥地復,逸興遄飛,有任公“世界無窮愿無盡”之感,但在新大陸的逍遙游之中卻難忘舊大陸的行路難,豪興之中又難抑悲愴,發(fā)而為文,慨當以慷,遂有高速而銳敏的風格;三來那幾年我對中文忽有會心,常生頓悟,幻覺手中的這支筆可以通靈,可以呼風喚雨,撒豆成兵,于是我一面發(fā)表《剪掉散文的辮子》一類文章,鼓吹散文革命,一面把倉頡的方磚投進陰陽的洪爐,妄想煉出女媧的彩石。
不管真丹有未煉成,爐火熊熊卻驚動了眾多論者。四十年來對我散文的評論約莫可分兩派,一派看重前期這種“飛揚跋扈為誰雄”的感興美文,認為真把倉磚煉成了媧石;另一派把這種銳敏之作視為青春痘現(xiàn)象,而強調后期之作醇而不肆,才算晚成。你若問我如何反躬自估,我會笑而不答,只道:“早年爐熱火旺,比較過癮。”
四
我寫評論,多就創(chuàng)作者的立場著眼,歸納經驗多于推演理論,其重點不在什么主義、什么派別,更不在用什么大師的學說做儀器,來鑒定一篇作品,不在某一“書寫”是否合于國際標準或流行價值,而是在為自己創(chuàng)作的文類厘清觀點,探討出路。
我當然也算是學者,但是并非正統(tǒng)的評論家,尤其不是理論家。若問我究竟治了什么學,我只能說自己對經典之作,也就是所謂文本,下過一點功夫,尤其能在詩藝上窺其虛實。文類的分野與關系,尤其是詩、文,也令我著迷。文學史的宏觀與演變更是我熟讀的風景,常常用來印證理論與批評。
說得象征些,我覺得讀一位船長的航海日志,要比讀海洋學家的研究報告有趣。同時,要問飛是怎么一回事,與其問鳥類學家,不如直接問鳥。
我所向往的評論家應有下列幾種條件:在內容上,他應該言之有物,但是應非他人之物,甚至不妨文以載道,但是應為自我之道。在形式上,他應該條理井然,只要深入淺出,交代清楚便可,不必以長為大,過分旁征博引,穿鑿附會。在語言上,他應該文采出眾,倒不必打扮得花花綠綠,矯情濫感,只求在流暢之余時見警策,說理之余不乏情趣,若能左右逢源,妙喻奇想信手拈來,就更加動人了。
反過來說,當前常見的評論文章,欠缺的正是上述的幾種美德。庸評俗論,不是泛泛,便是草草;不是拾人余唾,牽強引述流行的名家,便是難改舊習,依然仰賴過時的教條。至于文采平平,說理無趣,或以艱澀文飾膚淺,或以冗長冒充博大;注釋雖多,于事無補,舉證歷歷,形同抄書,更是文論書評的常態(tài)。
文筆欠佳,甚至毫無文采,是目前評論的通病。文學之為藝術,憑的是文字。評論家所評,也無非一位作家如何驅遣文字。但是評論家也是廣義的作家,只因他評點別人文字的得失,使用的也正是文字。原則上,他也是一種藝術家而非科學家;藝術的考驗,他不能豁免。他既有權利檢驗別人的文字,也應有義務展示自己文章的功夫。如果自己連文章都平庸,甚至欠通,他有什么資格挑剔別人的文章?“高手一出手,便知有沒有。”手都低了,眼會高嗎?筆鋒遲鈍的人,敢指點李白嗎?文采貧乏的人,憑什么挑剔王爾德呢?
我的評論文章或論文體,或評作家,或自我剖析,或與人論戰(zhàn),或為研討會撰稿作專題演講,或應邀為他人新書作序。年輕的時候我多次卷入論戰(zhàn),后來發(fā)現(xiàn)真理未必愈辯愈明,元氣卻是愈辯愈傷,真正的勝利在寫出好的作品,而不在曉曉不休。與其鞏固國防,不如增加生產。所以中年以后,我不再費神與人論戰(zhàn)。
倒是中年以后,求序的人愈來愈多,競為我的評論文章添了新的文體,一種被動而奇特的文體。序言之為文體,真是一大藝術,如果草覃交卷,既無卓見,又欠文采,則不但對不起求序的人,更對不起讀者,同時也有損自己的聲譽,可謂三輸,只能當作應酬的消耗品吧。因此我為人作序,十分認真,每寫一篇,往往花一個星期,甚或更久,務求一舉三得。對求序人、讀者和自己都有個交代。希望大陸的讀者不要以為這幾十篇序言,所薦所諫,多半是他們不熟的作家而草草掠過,因為我寫序言,不但對所序之書詳論得失,更對該書所屬之文類,不論是詩、散文、翻譯或繪畫,亦多申述,探討的范圍往往不限于一書、一人。
例如《從冰湖到暖海》一篇,就有這么一段文類論:“所謂情詩,往往是一種矛盾的藝術。它是一種公開的秘密,那秘密,要保留多少,公開多少,真是一大藝術。情詩非日記,因為只記只給自己看;也非情書,因為情書只給對方看。情詩一方面寫給特定的對方,一方面又故意讓一般讀者‘偷看’,不但要使對方會心,還要讓不相干的第三者‘窺而有得’,多少能夠分享。那秘密,若是只罕對方會心,卻不許旁人索解,就太隱私了。”
又如《不信九閽叫不應》里有一段論到用典:“用典的功效,是以民族的大記憶(歷史)或集體想象(神話、傳說、名著)來印證小我的經驗,俾引發(fā)同情、共鳴。用得好時,不但可以融貫今古,以古鑒今,以今證古,還可以用現(xiàn)代眼光來重詮古典。用得不好,則格格不入,造成排斥,就是‘隔’了……用典亦如用錢,善用者無須時時語人,此乃貸款,債主是誰;只要經營有方,自可將本求利,甚至小本大利,小借大還。”
……
余光中評說五十年 作者簡介
古遠清,教授 ,廣東梅縣人,武漢大學中文系畢業(yè),現(xiàn)為中南財經政法大學華文文學研究所所長,中國新文學學會副會長,代表作有《中國當代文學理論批評史》《臺灣當代文學理論批評史》《世紀未臺灣文學地圖》等專著。
- >
企鵝口袋書系列·偉大的思想20:論自然選擇(英漢雙語)
- >
我從未如此眷戀人間
- >
回憶愛瑪儂
- >
中國人在烏蘇里邊疆區(qū):歷史與人類學概述
- >
我與地壇
- >
有舍有得是人生
- >
小考拉的故事-套裝共3冊
- >
隨園食單